-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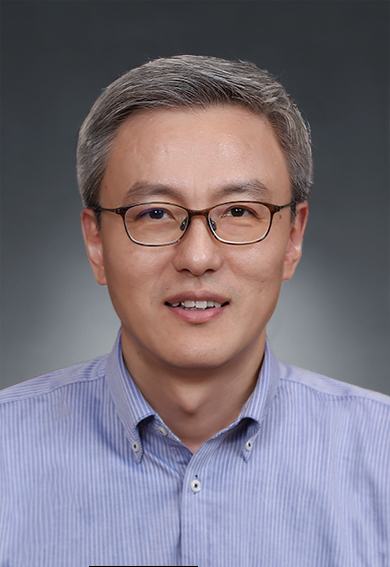
- 陈东晓
- 研究员
- 国际战略研究所
2018年是个非常独特的年份: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1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40周年……我们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点上抚今思昔,钩深致远,感受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国际格局正酝酿冷战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正拉开冷战以来大融合与大分化最激烈碰撞的大幕,不稳定和不确定风险突出将是可预见未来最显著的特征,国际秩序何去何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和时代之困。其中,三个趋势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第一,大国之间的战略不稳定正在加剧。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深。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大与俄罗斯在欧洲、中东等地区以及核导军控等领域的战略博弈,甚至局部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状态。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讲,通篇充斥着类似上世纪80年代冷战高峰时期美国总统里根对前苏联的指责,令许多中国人震惊和困惑。人们不禁要问:美国难道已决意要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世界是否将因此而被拉进一场新的冷战?
另一方面,除了华盛顿同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外,近年来大西洋关系也因为诸如伊朗核协议、北约军费分担、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龃龉不断而备受冲击,尽管尚未危及大西洋联盟的根本,但双方疏离感明显增加。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格局的基石,大国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正深刻影响着未来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走向。
第二,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正遭遇“失能和失势”的危机。以规则、协商和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及全球治理机制运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018年初以来,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和它的一些传统盟友发起关税战,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冲突。美国特朗普政府坚持所谓“美国优先”原则,为获取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几乎肆无忌惮地对贸易伙伴采取包括关税战在内的霸凌政策,甚少顾及这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对国际贸易体制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破坏。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以WTO为核心的、基于开放、规则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受到空前挑战,WTO自身也逼近“何去何从”的临界点。与此同时,自从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也面临严重阻碍。冷战结束以来,基于多边主义的规则和机制已经成为当下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曾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和维护者,如今正成为最大的影响国际秩序的不稳定之源。
第三,国家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政治认同浪潮正扑面而来。当冷战结束后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多年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勃兴的反全球化和反全球主义的思潮和运动,都与当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改革赤字密切相关。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这些思潮和认同政治的发展已经演变成某种“新部落主义”的泛滥,其突出的政治理念是排斥外来移民、戒惧国际贸易、敌视所谓“外来者” 对“自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包括外来的物流、人流以及思想流。这种认同政治的强化不仅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国家社会内部的分裂和政治极化的态势,并外溢到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所谓“我们”与“他者”之间身份认同的对立。
面对这些趋势,我们不禁要问:当今世界是否将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大分化? 如何有效管理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融合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相互之间的张力?国际社会的各利益攸关方能否通过集体努力来共同遏制这种紧张的加剧甚至失控?对上述问题恐怕没有简单和现成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努力,通过构建新的国际共识和拓展共同利益,来缓解大分化的压力。
首先,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阻止冷战的幽灵从历史的废墟中死灰复燃。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对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大国之间对抗冲突的案例进行了梳理,其中包括不少因决策者的战略失误而导致的悲剧,并总结出不少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彼此误判对方的战略意图;彼此错误处理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忽视国际关系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即一国政府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或为转嫁国内深层矛盾,煽动所谓“外敌意象”,从而导致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不断恶化。如今,一些美西方人士继续沉溺在赢得冷战胜利的怀旧中,甚至幻想着通过挑起又一场所谓对华新冷战从而使得美国重新强大。我们能否真正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拒绝冷战的诱惑,避免大国对抗的陷阱?
其次,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合作,遏制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侵蚀,同时更积极地推动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全球治理
当前,对全球化的不满明显增加,对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的失望也日益增长。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有不断绷紧之势,如何使得两者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是当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迫切需要解答的难题。但有一点显而易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世界而言,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和跨国威胁,单边主义绝不是好兆头。实行单边主义对单个国家而言也许有其吸引力,但由此所产生的麻烦将远多于其想解决的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合作应对是唯一出路。
最后,国际社会需要创新思维,推动构建新的集体意识和认知共识。当前关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国际话语结构中,主流的叙事方式和分析框架依然是基于权力政治的逻辑和认同政治的逻辑。尽管上述叙事逻辑依然具有其一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但已经无法涵盖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演变方向。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分析框架,我暂且称之为“发展政治”的逻辑,以便能更全面地把握世界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发展方向。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无论是全球化的发展还是国际秩序的演变将同当前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正在进行的后现代的再平衡进程走势密切关联。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前一个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美国和欧洲等在后一个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就前一个进程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席卷了非西方世界。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初步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根据世界银行报告的数据,在世界银行189个成员国中,有将近40个国家是发达经济体,在其余150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08个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总人口超过55亿人,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这其中约有40个国家是中上收入国家。
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基础上集聚力量,开启向中高级现代化迈进的新征程。这一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新一轮现代化取得成功,意味着未来20-30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之外的超过40亿的人口将成为中产阶级,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空前的现代化,因为其影响到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和历史意义都远远超过前两个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世界能否顺利步入更为先进的现代化阶段也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又一道时代之问。一方面,规模的不同、历史及现实环境的差异,发展中世界已经无法简单复制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从发展中国家国内角度看,它们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结构的不断完善。来自外部的挑战主要是由西方主导的现有的国际体系是否能够容忍和容纳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作为一个由现代化向后现代阶段转型、过渡的整体,在冷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浪潮的席卷下,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同样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内部发展和治理的转型压力,进入了我称之为的“后现代化的再平衡时期”。其中一个突出的表征是,总体秉持开放、包容和竞争原则、具有鲜明全球主义指向的力量,同基于保护和注重平等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的力量之间相互角斗,他们分别代表了所谓“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受益者”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受害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不但加剧了西方内部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而且加速反噬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启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作为一个整体,西方世界迫切需要同时对自身国内治理和推动国际乃至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就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等治理而言,西方世界应该通过自身的改革,提升其体制支持内部包容、普惠以及均衡发展的能力,以此保持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稳定,从而能够协调所谓全球主义者同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者之间日益对立的关系。就其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而言,西方世界特别是其领导力量应该认识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意义,通过不断完善内部体制和扩大现有国际体系的包容程度,来推进整个世界现代化和世界和平繁荣的进程。
当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转型进程相遇时,两者究竟是以包容、稳定、合作的方式互动,亦或是排他性、对抗性、混乱的方式互动,将对世界政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换言之,未来世界究竟走向大融合还是大分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的后现代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能否都取得成功,以及相互之间以何种方式互动。
因此,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新的共识,在分与合相互激荡的世界里同舟共济,一起探索和开辟一条共同发展的和平繁荣之路。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者而言,这是挑战,更是使命。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