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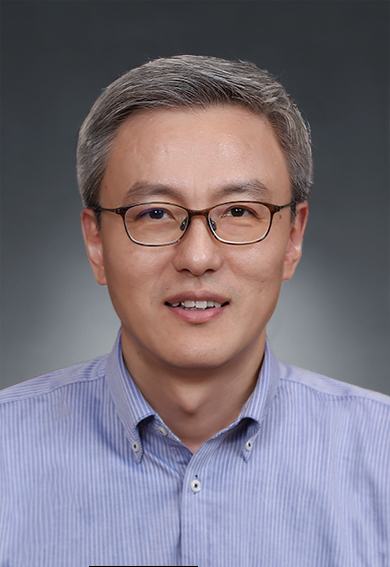
- 陈东晓
- 研究员
- 国际战略研究所
-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打造绿色军队:美国军事能源战略调整评析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美中东政策比较——理念、政策与贡献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从三个方面看美国大选
- 香格里拉对话会防务外交的实质是什么?
- 中美需要保持高级别、全方位的战略对话
- 中国领导人12年来首访埃及 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再添活力
- 中俄关系2015:高调前行、道路曲折
- 习主席访问埃及的三重意义
- 特朗普上台 蔡英文台独梦灭
- 起点•亮点•重点——中非合作进入新阶段
- 三个“非常”好的中津关系
一、当前大国关系战略环境的新态势
首先,国际权势的“多极化”和“均衡化”的基本态势将持续。国际力量格局正加速从传统的以美欧为中心向着多中心的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2]特别是经历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了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得势”力量(或称之为“关键影响力中心”)、以美国为代表的“守势”力量、以欧、日等为代表的“失势”力量,以及包括南非、土耳其、印尼等一批地区重要力量(或称之为“新兴影响力中心”)的国际力量变化的新雏形。[3]其中,美国单极独霸图谋已严重受阻,垄断国际事务的难度继续增加。但同时,奥巴马政府着手内政外交的所谓“变革”,努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从综合实力,尤其是国际机制的制定权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方面分析,美国仍在可预见的将来处于“超强”及“首要”(primacy)地位,这一主张普遍被美国主流学者所认同。[4]欧洲(英、法、德为代表)、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不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还面临生产效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等长期困扰,但也力图扭转“失势”局面,希望加快各自经济结构转型步伐,推进区域整合和跨区域的合作,争取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竞争优势,在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保持其影响力。[5]而中、印、巴西等新兴(或复兴)大国则抓住机遇,加快转化、扩展在危机中的“得势”效应,进一步提升各自在新一轮国际机制改革及创制中的话语权,力争使其制度化。2010年4月世界银行改革投票权,将欧洲小国投票取转移给中、印、巴等即是典型事例。总之,未来5-10年内,国际力量多极化、均衡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多强之间相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正成为国际权势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迫切需要以及全球治理的“两重性”特征强化了大国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特征。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协调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面,大国合作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挑战已经成为各大国领导人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不断宣示的中心思想。[6]我们看到,在危机时期,传统和新兴大国对国际体系重组达成了在“维持中改造”的共识,在危机时期大国运用“互不挑战的精神”、“合作共赢的原则”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重演,产生了较强的延伸和示范效应。[7]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传统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仍将延续危机时期以合作为主、竞争为次的总态势。但另一方面,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发展空间的分配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经济社会影响仍在显现,世界经济仍处于脆弱的复苏阶段,各大经济体纷纷将保持本国经济增长和提高本国就业视为政策首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持续上升。[8]面对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气候变化对发展模式转变及发展空间的压力、以及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中对原有利益的触动或重新分配等敏感问题,各大国或集团服从国内大局考虑的压力急升,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增加,竞争明显加剧,尤其在使二十国集团(G20)成为世界经济治理中心的机制化问题上,大国之间出现了矛盾上升、合作意愿消退的迹象。对此,加拿大学者库珀和布拉德福特观察指出,“各国政策协调的矛盾限制了(G20)架构的前进步伐”,“随着金融危机冲击的消退,保持大国领导人对集体事业的持续关注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而(G20)内部出现的派别进一步削弱了集团的集体精神”。[9]
第三,受新一轮国际力量变化和全球治理需要的驱动,大国重新“集团化”(Grouping)正成为大国互动的新态势。一是集团形态更加多样,冷战时期整体性的结盟继续存在,并呈加速转型、扩展之势譬如北约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的发展,以适应地区和国际安全的新要求;与此同时,针对具体问题的功能导向型合作(如针对伊朗核问题的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德国的所谓“P5 1”进程)和领域型大国集团(如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出现的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基础四国”)正成为当前大国重新集团化的主流。二是集团驱动力日趋多元,正超越单一的意识形态纽带,以应对更为严峻的各种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谋求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三是集团间关系性质发生了变迁,从冷战时期以对抗为主,到目前零和性质大幅降低,集团之间呈现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制衡的复杂状态。四是机制化水平各不相同,既有机制化水平较高的传统同盟、大国集团如G7/G8,也有仍属于对话论坛性质的如“金砖四国”等会晤机制,未来各种集团将朝着多元而非单一的机制化方向发展。五是各集团内部的领导权模式的演变,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主导,开始向集体协调的模式转变。[10]六是大国虽然认识到改革国际体系和构建刚性机制的重要性,但鉴于“完全一致”的困难和通过表决投票来运行的刚性机制往往行动能力不足,大国大多倾向通过G8、G20、金砖四国等所谓“G-x”进程以及各种区域峰会等“治理网络”来协调相互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较快形成的大国共识来塑造国际舆论,另一方面为各国保持了在全球性和地区性体系重组时的主动性和选择性。[11]
二、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当前和今后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与大国关系在相互合作中继续竞争、相互借重中保持防范的互动模式将持续,但在新的国际局势和战略环境的催生下,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利益重组及磨合期。其中,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努力延续危机时期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为主的关系态势同时,也暴露出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继续提升机制性合作水平同时,新旧矛盾的复杂影响也在加剧。
首先,中国的利益拓展已触及大国实质甚至重大利益,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势变化加剧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态和战略疑虑。中国综合实力和利益拓展的高歌猛进、外交领域的节节胜利、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内外挑战的体制优势增加了美国的警惕,也大幅度提高了华盛顿方面对中国与美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期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舆论一度热捧“中美共治”(G2)概念,即是美方的典型反应。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领导角色”,较之于布什政府时期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又更进一步,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所谓维护国际体系的责任。[12]相对而言,欧洲、日本等金融危机中的“失势”大国失落感和危机感增强;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也担心在后金融危机的秩序重建中拉大与中国距离,对中国实力增长及利益拓展的疑虑都有所增加。[13]欧、日、俄、印等国的舆论也不同程度地对中美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性合作日益拓展的前景,特别是所谓“中美共治”(G2)表达疑虑和不满。[14]尽管“中美共治”论颇有媒体炒作之嫌,但也表露了这些大国担心甚至不满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传统影响“被边缘化”的情绪。
其次,中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传统西方大国)互动模式的调整导致相互之间的不适应矛盾有所凸现。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综合影响力持续跃升以及积极、主动外交的不断开展,一些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在继续疑虑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意图的同时,更多地对中方“积极有所作为”开始“不适应”和“不舒适”。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在议程设置的积极性、要求平等的迫切性、以及塑造中美关系的主动性方面有了较明显地提升。中美之间从先前中方主动调适对美关系的互动态势,转向了要求美国更多地向中国调适其对华关系,加剧了美方对双边互动模式变化的不适应。[15]华盛顿方面开始对其可能丧失中美关系的主导地位的疑虑和不满明显上升,并利用其主导的西方舆论,掀起新一轮对所谓中国的“强势外交”、“傲慢外交”、“误判形势”的口诛笔伐,[16]力图扭转对华关系中的被动局面。2010年以来,美国舆论围绕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天安号事件”、黄海军演、南海海上航行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推波助澜地要求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显示强硬和决心。[17]
一些欧洲大国也遥相呼应,批评中国对欧洲“双重标准”、“欺软怕硬”。[18]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的新兴大国也从各自战略利益和实际关切出发,一方面加紧与其他大国的合作联系,以防范、制衡所谓中国“强势外交”对它们国家利益的损害,另一方面呼吁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要更加自信。[19]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中国与大国之间固有矛盾和被推迟、掩盖的新旧利益分歧集中爆发的心理准备有所不足,对美国策动西方媒体炒作和放大“中国傲慢论”尚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加之国内一些媒体散布的极端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情绪,也增加了中国社会适应新的对外互动模式的困难。
再次,中国与主要大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大国)之间自身份定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双方对所谓“核心利益”与“(国际)体系利益”的认知差距被放大,政策协调难度增加。
一方面,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强调把主权和领土完整纳入中国核心利益的诉求具有正当性,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肩负的长期历史任务。但在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在如何界定“核心利益”概念上尚未有共识,[20]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中国在领土要求上得寸进尺”,[21]部分舆论甚至将中国捍卫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的决心解读为“中国开始扩大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认为中国意欲“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要求奥巴马政府转变战略以“保护现行体系的有效运行”。[22]
另一方面,中国以发展中国家来界定自身在解决全球核地区问题时所承担的职责,强调中国在维护“(国际)体系利益”过程中坚持公平、适度和渐进的原则,承担与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23]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排,并切实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是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的关键。但是美、欧等西方大国不断抬高中国的大国身份,要求中国以“核心大国”的身份重新定义核心利益,大幅度提高承担维护“国际体系利益”的国际责任,一些西方舆论甚至要求中国在诸如“世界经济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领域扮演领导角色。[24]应该看到,美国制造出“中美共治”舆论,既反映其在国际事务中增加对中国倚重的客观事实,也希望以此来分担美国的领导成本;欧洲大国则希望继续在气候变化、发展援助等机制建设和话题引领上保持主导权。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在核心利益认知上的差距短期内难以缩短。
第四,大国对外政策导向的调整,增加了各自重大政治让步的难度。尽管世界经济进入脆弱恢复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大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压力凸显,大国从危机时期强调国际合作不同程度地向服从国内政治议程的方向调整,一些大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政治意愿消退,各种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应运而生,经贸摩擦政治化的频率和强度明显提高。尤其是美国为了转移自身的失业压力的矛盾,一方面威胁要对中国的所谓“货币操纵”行为实施制裁,同时还联手欧洲、印度、巴西等国,并谋求在IMF、G20峰会等各种多边场合,策动议题联盟,多管齐下对中国施加压力。[25]
第五,以中国为代表的复兴大国/兴大国在危机期获得突破性机遇后进入常态博弈期,用建章立制的方式使西方在危机中的表态性让步迅速转为实质性让步的困难也随之增加。大国关系从危机时期在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协商疲劳期。随着传统大国走出危机后让步意愿逐步减退,在北强南弱和美国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举步维艰,G8和G20的相互关系前景不明即可看出这点。此外,大国关系的主要议程从危机时期西方暂处下风的金融安全向西方更为强势的议题转移,如核不扩散、核安全、气候变化等。随着中国与美欧等大国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和核安全三大战略性议题互动相继进入协商常态化和斗争长期化阶段,短期内双方在上述领域合作获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降低。
三、新时期发展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全面成长中的复兴大国,近十多年来始终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大国是关键”的战略部署,全面发展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关系,不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战略布局的深刻内涵,使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发展不但适应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
首先,要继续坚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同舟共济的精神指导下全面发展与各主要大国的关系。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发展,全面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对新时期中国的整体外交以及整个国家发展战略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有也更有能力和潜力继续推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关系。尽管国际力量的发展态势正日益多极化和均衡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国仍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占有者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国是国际体系的改革与转型的核心力量,是应对日益尖锐复杂的各类全球问题的主要行为者。没有良好的大国关系,中国和平复兴所要求的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舆论环境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公共问题挑战日益严峻,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不断加强,大国合作共同应对、治理全球问题的战略意义日益凸现,大国合作的空间也不断扩展。同时,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各国对中国的战略倚重必然持续提高,从而为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以及互利共赢奠定了基础。
其次,明确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多层次战略定位,加快形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其它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相互支撑的战略布局。
新时期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期待和要求,同时在中国与大国关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诚如2009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中所言,“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中美“(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6]中美关系的这一定位说明,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在应对、治理全球问题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正被赋予新的内涵。继续在战略上稳定中美关系,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中发展中美关系,将有助于提升我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扩大中国塑造国际秩序影响力。
中美关系固然在我大国关系中至关重要,但美国对中国复兴的战略怀疑和战略牵制、包括美国售台武器在内的对中国核心利益的破坏等不利仍然不时阻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使得中美关系难以成为最健康和最稳定的大国双边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更紧迫的战略需求和能力发展与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等其它重要国家的关系,通过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等多个渠道,谋划更加均衡和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的布局。
一是要继续推动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均衡发展。中日双方应进一步以亚洲为主要舞台,密切在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协调,包括区域金融安全和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等的区域中合作,强调地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感,为中日关系提供强劲的战略依托。
二是要正确认识欧洲在国际格局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欧洲尽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是国际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应对全球各种挑战,改善全球治理方面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2009年第12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所言:“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在国际问题上拥有诸多共识,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和繁荣”。[27]我们需要不断深化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内涵,为新时期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夯实思想基础。
三是要积极应对中俄务实合作进入结构转型和战略升级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突出中俄共同肩负维护国际格局多极化,促进国际和平和发展、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的历史使命,努力把中俄关系发展成熟、稳定、健康、充满活力的大国关系典范。
四是要在努力突出中印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认同,从中扩大双方在未来国际体系建设中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重视双边渠道扩大与印度的经贸联系,提高在多边经济机制建设过程中双方的政策协调水平。
第三,加强新兴大国多边合作机制的运筹,积极构筑中国的大国关系的战略支撑。
正在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无论是复兴中的大国还是日益具有国际乃至全球影响的区域性强国,都是国际体系改革和构建中的最具活力的力量所在。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新兴大国一方面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缺乏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利益表达的国际机制表示不满,另一方面,新兴大国普遍表示将通过对现有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机制化地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权益。在此过程中,新兴大国同时还面临着国际体系内传统强国的各种牵制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压力。但是新兴大国的机制化合作的意愿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成为当前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4月出席在巴西利亚的“金砖四国”第二次首脑峰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四国政治体制、发展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却能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充分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历史文明可以相互借鉴,不同文化传统可以相互交流。[28]中国要进一步与其它新兴大国一道,从战略高度明确合作方向,以政治互信为基石,以务实合作为抓手,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开放透明为前提,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培养共享价值观,逐步使新兴大国的对话机制成为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可以依赖的战略支撑。
文献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注释:
[1] 本文中的大国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传统西方强国,也包括诸如俄、印度、巴西等正处于复兴或崛起中的大国。尽管欧盟一体化仍处于演进之中,内部分歧矛盾仍时时爆发,但人们大都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因此涉及中国与欧洲的大国关系时,它既包括与英、法、德等传统强国的双边关系,也包括与欧盟整体的关系。[2] 目前国内外对于国际权力究竟是向多中心方向扩散还是“集中向一个方向转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林利民认为“确认世界‘权力东移’已是基本共识”,见林利民:《世界地缘政治新变局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第1-2页。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则不认同“世界权力重心东移论”,详见中国外交部网站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720868.htm (上网时间:2010年8月7日)。
[3] 关于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态势中出现的“得势”、“守势”、“失势”等力量格局的阐述,最早由杨洁勉提出,见杨洁勉:《当前国际战略态势和国际形势特点》,《国际展望》2009年11/12月,第1页。2010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正在复兴和崛起的大国称为“关键影响力中心”(key centers of influence),将印尼、南非等称为“新兴影响力中心”(emerging centers of influence),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3, P.7, P.11, pp. 40-44.
[4] 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2010年5月24日在上海国研院同中方学者座谈时强调“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垄断地位难以为继,但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首要(primacy)作用”;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著名主持人扎卡利亚2010年6月4日在上海国研院同中方学者交流时也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以欧洲而不是美国的衰弱为代价。” 美国政治学者戴维·兰普顿则从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关于各国GDP占全球比重变化分析得出,美国在2002年达到最高点,占当年世界GDP的30.67%,到2009年,其比例为29.26%,只下降了1个多百分点。相对而言,欧洲(欧盟15国)在1969年达到其在全球GDP份额的顶点,比重为35.78%,2009年为27%;日本1982年达到比重的最高点,为11.08%,2009年为8.69%。因此尽管当前美国遇到严峻的困难,但(经济)实力并没有严重受损,“真正失去份额的是日本和欧洲,而不是美国”,“绝不能低估美国及其自我更新的能力。”见戴维·兰普顿:《中美关系中的力量与信任》,《国际展望》,2010年7/8月,第43-44页。
[5] 关于欧洲是否在衰弱以及欧盟能否使欧洲重新成为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国内外学者意见分歧较大,悲观派认为欧洲正处于“漂移和危险境地”,甚至是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力量”,中间派认为欧洲短期内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综合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未来中长期发展向好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乐观派认为欧洲是未来国际体系中唯一能和美国并驾齐驱的一极。参见 Walter Laqueur, etc., “Can Europe Recover? The Fading Promise of an Aspiring Superpower”, The American Interests (电子版), July/August, 2010(上网时间:2010年8月11日); 裘元伦:《不应过于唱衰欧洲》,http://ies.cass.cn/Article/cbw/zdkycg/201007/2727.asp(上网时间; 2010年8月11日);Anthony Luzzatto Gardner and Stuart E. Eizenstat, “New Treaty, New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0; Andrew Moravcsik, “Europe, the Second Superpower”, Current History, March, 2010.
[6] 例如金融危机后的二十国集团多次的峰会宣言都突出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合作、同舟共济的意愿。在诸如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中欧领导人会晤、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等双边或多边场合,合作应对全球问题也是各国领导人的基本共识。
[7] 例如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尽管包括俄罗斯、巴西、中国等都通过不同渠道严厉批评了以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合理性,但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仍然坚持在维护现有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改革,那些要求迅速结束美元主导的方案并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
[8] 根据欧盟委员会2010年7月发布的第六份《潜在贸易限制措施报告》得出结论,二十国集团在经济危机中引入的贸易限制措施呈稳定持久的趋势。贸易壁垒中所谓的“安静的扩散”构成重要的系统性挑战。参见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网站:《欧盟委员会公布最新贸易壁垒监控报告》,2010年7月27日,http://www.sccwto.net/webpages/WebMessageAction.viewI(上网时间:2010年8月11日)
[9] Andrew F. Cooper and Colin I. Bradford, Jr, “Confronting the Architecture Demands of Global Leadership: The G20 and Post Crisis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for the CIGI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sues for 2010 Summits, 3-5 May, 2010, Waterloo, Canada.
[10] 美国观念转变对于大国集团领导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美国一些重要智库和有影响的专家近年来不断强调“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地保护自己免于它所面临的一系列威胁”,“主要大国之间的基本一致也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需要在大国之间开展“多次互动性进程”。见布鲁斯·琼斯等:《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中译本,秦亚青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3-45页。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在其所提倡“多伙伴”战略中强调大国协商的重要性,见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2009年7月15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讲话,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071.htm(上网时间:2010年8月15日)。
[11] 长期研究八国集团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加拿大学者约翰·科顿观察指出,在G-x”进程下出现的这种网络将同等数量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纳入进来,(此治理网络)按照共识原则,而非按照一致通过原则所要求的正式的、具有法律约束的投票表决来运行,但从应对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效果来看,治理网络比之1997-1999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机构的应对更为有效。参见John Kirton,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Network Governance”, in Alan S. Alexandroff and Andrew F. Cooper eds., Rising States, Rising Institutions: Challenges for Global Governa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2010,pp. 196-213.
[12]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 43.
[13]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2010年4月25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者亚历山大·卢金发表在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网站的文章《北京对外政策——新的转变?》;2009年12月1日巴西圣保罗大学巴西问题研究所经济史学教授巴尔博萨发表在《耶鲁全球化》网站上的文章《与龙共舞》;印度防务分析研究所网站2010年2月17日发表该所研究员杰哈的文章《发展一种战略模式》。
[14]例如Marcus Walker, “EU sees Dreams of Power Wanes as G-2 Rise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NA_WSJ_PUB:SB10001424052748704905604575027094159815012.html(上网时间,2010年8月6日); 2009年3月12日俄罗斯政治新闻社刊登伊戈尔·扎当的文章《两国集团?》称,“中美两国集团将使俄罗斯成为第一个受害者”,http://www.apn.ru/publications/articles21432.html (上网时间, 2010年8月6日) ; 2009年8月6日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叶夫盖尼·巴扎诺夫在俄《独立报》发表《两极世界——美国的幻想》一文中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两极世界是美国的一个幻想”,http://www.ng.ru/politics/2009-08-06/3kartblansh.html(上网时间,2010年8月6日); 日本《选择》月刊2010年3月号刊登《七国集团将沦为乌合之众》文章称,日本外务省正秘密推进一项研究,目标是就加强与欧洲合作,与美中两国(G2)抗衡。转引自《日刊说日本不应沉迷旧日辉煌并同七国集团一起被埋没》,《参考资料》,2010年3月29日;以及Swaminathan S Anklesaria Aiyar,“It is Goodbye Chindia and Hello Chimerica,”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home/opinion/sa-aiyar/swaminomics/Its-goodbye-Chindia-and-hello-Chimerica/articleshow/4419231.cms.(上网时间2010年8月6日)
[15] 格雷格·托罗德在《南华早报》2010年6月29日发表《两个世界之间》一文中引用美国民主党一位资深专家的话说,“北京的外交远比我们印象中更加咄咄逼人——实际上他们自信到了挑衅的程度。他们感受到了自身的影响力并已准备好利用这种影响力。至少需要我们稍作适应。”转引自《托罗德说中美短期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但前景如何尚难断定》,《参考资料》2010年7月16日。
[16]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约瑟夫·奈的《中国针对美国的糟糕赌注》,刊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010年3月10日;潘文2010年3月15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新崛起的中国在语言和政策上藐视西方》;2010年2月1日《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编辑纳扬·昌达发表的《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等。
[17] Daniel Blumenthal, “The U.S. Stands Up against China’s Bully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7, 2010,
http://online.wsj.com/article/NA_WSJ_PUB:SB10001424052748703700904575391862120429050.html.(上网时间, 2010年8月6日)
[18] Francois Godement, “China’s Apparently Cost Free Slight to Europe”, PacNet No.65, Pacific Forum, CSIS, December 9, 2008.
[19]例如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者亚历山大·卢金4月25日发表在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网站的文章《北京对外政策——新的转变?》中称,鉴于中国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考虑俄中关系和俄对外政策的基础”,“为了保持平衡,(俄)必须发展与这一地区和世界上其他玩家的密切关系”。转引自《卢金称中国出现新外交思想俄应重新考虑对华关系和政策》,《参考资料》2010年5月20日;印度的军事分析专家哈里哈兰在南亚分析集团网站2009年10月8日发表《诚实面对中国在南亚的势力》一文中称,“(印度)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态度很谦卑,而不是抢占先机、明确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呼吁印度要“以平等地方式应对中国”。转引自《参考资料》2009年11月18日。
[20]例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观察道:“中美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双方尚未对此进行界定,这将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参见“Obama is Playing Nice with China”, i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ovember 25, 2009,
http://politics.usnews.com/news/articles/2009/11/25/obama-is-playing-nice-with-china.html (上网时间,2010年8月6日)。
[21]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的麦克·理查森2010年3月14日在《日本时报》发表《缓解中国日益强烈的“核心”担忧》一文时称,“包括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在内,中国的部分邻国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北京是否及何时会扩展自身核心主权利益?”转引自《理查森认为美日印等国需要认清中国的核心主权利益》,《参考资料》,2010年3月24日。
[22]托马斯·赖特《美国必须找到新的对华战略》,英国《金融时报》8月9日,转引自“美学者:美需找到新的对华战略”,《参考消息》2010年8月12日,第16版。
[23] 杨洁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2009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wjbz/zyhd/t649125 (上网时间, 2010年8月6日);甘均先:《“中国责任论”解读与中国外交应对》,《国际展望》,2010年7/8月号,第66-69页。
[24] Francois Godement, “A Global China Polic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2, 2010, http://ecfr.3cdn.net/126014f261f60e93c0_bam6ib6zd.pdf (上网时间, 2010年8月5日)
[25] 《美国议员联名要求人民币升值信函原文》,经济观察网,2010年3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00316/13517573907.shtml (上网时间, 2010年8月6日);《日本产经新闻》2010年6月6日刊登《G2论创始人主张用多国框架消解美中摩擦》的报道,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认为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中国已变得越来越不合作”,“美国应该认真考虑组建‘反中国阵营’”等多边方式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转引自《伯格斯滕称美应组建“反中国阵营”用多边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参考资料》2010年6月9日。
[26]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北京2009年11月17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上网时间,2010年8月6日)
[27] 《第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新华社南京2009年11月30日电,http://www.gov.cn/jrzg/2009-11/30/content_1476644.htm (上网时间,2010年8月5日)
[28] 《胡锦涛出席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并讲话》,新华社巴西利亚2010年4月15日电,http://www.gov.cn/ldhd/2010-04/16/content_1583336.htm (上网时间,2010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