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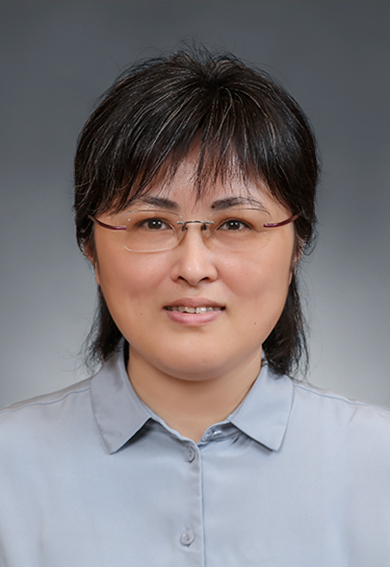
- 吴莼思
- 副研究员
- 美洲研究中心
- 国际战略研究所 所长
-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中美中东政策比较——理念、政策与贡献
- 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 — — 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原因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中俄关系2015:高调前行、道路曲折
- 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
- 中国智慧与力量造福世界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
- 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新旧困难
-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智力支撑
- 中国外交新思路 新实践 新理论
-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中国外交:今年成绩超出预期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中国外交与和平发展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国家民族”建构研究
-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 欧盟社会政策研究
- 《老挝与“一带一路”》
- 《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
- 《国际体系演进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 上海服务中拉合作的现状与趋势——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上海角色
-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经典案例2021
- 上海服务东盟地区“一带一路”建设 逆势成长与新挑战
- 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
- 中美关系正常化历史上的四次关键战略协作的启示
- 美国区域经济合作倡议的内涵、反响及前景
- 错失良机的悲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损失
- 更多错失良机的悲剧:新冠疫情中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力和经济损失
- Working Together with One Heart: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 中东地缘政治新博弈与全球战略态势调整
第一,2003年前后阿富汗、伊拉克战事正酣,小布什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应付新形式的安全威胁即恐怖主义上。美国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卷入了一场长期战争。进入21世纪后,美国面临紧迫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恐怖主义威胁;二是全球性威胁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网络、深度保卫国土、在国家处于十字路口的背景下作出合理的战略选择、防止敌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目标。尽管提及信息网络,但报告主要将其视作美国军力配置的优势要素之一。[4] 尽管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内遭到很多批评,但作为这几场战争的发动者,小布什政府很难作出战略调整。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客观地讲,经过近十年的反恐行动,美国本土遭受恐怖主义直接打击的风险有所下降。2011年5月,美国击毙了被认为应该为“9·11”事件负责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进一步为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合法性。其次,奥巴马总统本人始终反对伊拉克战争,他对于调整战略主导方向没有负担。于是,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逐渐摆脱“9·11”事件的阴影,开始寻找新的战略命题。
第二,在美国将要调整战略重点的关键时期,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为开端,美国陷入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来说,不仅导致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震荡,更引发了政治、社会、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的反思。在安全战略方面,美国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2009—2011三个财年年度财政赤字连续超过1万亿美元,[5] 美国政府面临着缩减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政府预算的巨大压力。2012年1月26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莱昂·帕内塔宣布在未来5年内削减10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未来10年内将减少4,870亿美元军备开支。[6] 在此背景下,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在全球全面投射战略力量的“优势”(primacy)战略[7],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控制全球的“通道”上。由此,波森教授在2003年呼吁的“控制公域”最终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必然选项,海洋、大气空间、外空和网络空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
与上述两个客观事实相并存的是,美国事实上在诸多公域拥有重大优势。因此,推动美国战略聚焦转向公域的,或许并非上述客观事实,而是更深层次的主观关切。笔者认为,这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公域焦虑,它很大程度上与以中美权势转移为核心的整个国际体系转型密切相关,反映出美国对霸权衰落的深层次战略焦虑;如果说中美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战场”的交锋已呈胶着状态,那么美国战略聚焦向“公域”问题的转变本身便是一种开启“新战场”的努力。如何认识这一“新战场”的表象与实质,如何作出正确且恰当的战略应对,已经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美国战略焦虑的表现与实质
与国际社会不同,美国战略界更多是从战略和军事意义上讨论公域问题,因此可被称作“全球战略公域”。客观上看,美国在全球战略公域拥有如果不是无可匹敌的至少也是重大的优势;但主观上,美国仍焦虑重重。究其实质,乃是对霸权衰落的深层次战略焦虑主导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公域观。
公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讨论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研究的进展。冷战结束后,大国对抗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跨国界、全球性问题引发更多关注。其中,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维护能源和粮食市场安全以及保障南北极的和平稳定等议题都涉及如何管理主权管辖之外的“公共领域”问题,使公域成为国际事务中的热议话题。[8]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战略界关注的公域问题并不等同于全球治理语境中的公域问题。2010年,莱登(Mark E. Redden)和休斯(Michael P. Hughes)在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所的刊物中写道:“全球公域这一术语最初来自民用部分,它逐渐成为‘极地、公海和深海矿产、大气层以及外空’等区域的总称”。[9] 2013年,新美国安全中心全球公域报告的主要撰写者登马克(Abraham M. Denmark)在一篇讨论中美关系与全球公域的文章中指出,“在诸如社会交往、气候变化以及全球贸易等问题上接触当然是值得的,而且双方(中美)对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大致轮廓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尽管这些领域有重大的政治效应,但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导致双方的危机和冲突。……当中国持续崛起而美国寻求维护和加强其在亚太的权力时,全球公域——这些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相互链接作用却又无人管理的范畴——正是互动中可能迅速导致误解、危机和冲突的区域。”[10]
可见,对于美国战略界来说,全球治理人士所热衷的气候变化等议题,并不包括在他们的公域概念中。美国战略界关注的公域问题,是那些会导致危机和冲突的区域,是那些非民用的议题,是那些有特定防范对象的领域。因此,正如有些学者十分准确地指出,对于美国战略界来说,“‘公域’这个词起源于马汉在其《海权论》中对霸权国控制海洋产生的战时商业利益的分析”。[11] 美国战略界关注的公域问题并非“没有威胁者的威胁”,[12] 而是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是与维护美国现在以及将来的权力地位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美国战略界使用的公域概念与全球治理研究中讨论的公域问题区分开来。美国战略界在现实主义权力博弈框架中讨论的公域问题,也许可以称为“全球战略公域”,[13] 主要指美国国防部报告中所论及的海洋、大气空间、外空和网络空间四个范畴。
可以认为,美国在使用全球战略公域方面相当自由。在海洋方面,美国在一战后通过《五国海军条约》获得了与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14] 二战后,欧洲和前苏联都受到重创,美国拥有进一步谋取战略优势的资本,这在海军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个两面向洋的海洋国家,美国在发展海上力量方面具有苏联难以匹敌的优势。而且,美国的商业利益横跨全球,成为使用海上力量的巨大经济推动力,这也与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地区的苏联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尽管苏联在冷战两极格局下可依靠核潜艇等少数战略项目与美国抗衡,但总体上美国更加主动且能控制全局。美国由12艘航母为基础的庞大海军力量、众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及同盟关系共同构成了“自由”使用海洋的能力,使其迟迟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认为自己已强大到无法接受条约束缚的地步。
从空中力量来看,美苏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将争夺制空权的斗争延伸到了外层空间。虽然在人类进入外空时代的最初阶段,美国一度相对被动,但是很快就通过重设目标和重组项目扭转了局势。[15]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更是通过“星球大战”等计划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将其一步步推向解体。目前,尽管由于航天飞机老化、预算吃紧等问题而呈现发展放缓态势,但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外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截至2001年底,美国拥有近110件现役军用航天器,占轨道上运行的军用航天器的2/3以上。俄罗斯远远落后,约有40件。其他国家只有约20枚卫星在轨。[16] 迈克尔·欧汉隆也指出,美国在军用卫星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唯一能与美国相比的是俄罗斯,但俄罗斯的全球定位系统(GLONASS)尚未完成,其早期预警系统的卫星只有一半处于工作状态,2/3的卫星已超出设计使用年限。其他国家如欧洲国家、日本和中国,尽管拥有一定规模的外空项目,但其卫星无论是数量还是多样性上都远远落后于美国。[17]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美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用外空资源重新整合军事力量、改变作战方式、提出新作战理论的国家。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其海外军事行动中扩大了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作战方式越来越向精确打击和非接触攻击的方式演进,这显然与其拥有巨大的空中和外空力量优势是分不开的。
在网络空间,美国也占据很大份额。目前全球使用的互联网是由美国军用网络发展而来,美国对该系统的认识远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刻。连接全球网络系统的13台根服务器,1台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12台副根服务器中9台在美国,另外3台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全球互联网用户的域名由接受美国商务部授权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控制。[18] 可见,美国实际上控制着当前全球互联网系统的主干和神经。
可以认为,在美国所界定的四个全球战略公域内,美国都拥有全面优势。那么,为什么白宫和五角大楼仍不断发出全球战略公域受到挑战的预警?美国的这种战略焦虑究竟从何而来?笔者认为,美国的战略焦虑根本上源于这一主观认知,即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美国发现其长期以来在全球战略公域中所拥有的特权和垄断地位正面临着缩减和消失的危险。的确,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在全球层面快速铺开,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具备了进入全球战略公域的能力。大量新行为体进入全球战略公域,使美国感觉到其活动空间正在缩小。
外空方面,逐步迈入外空时代的国家已经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日本和中国这样的传统大国,巴西、韩国以及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外空发展计划。更有甚者,长期被美国视为“问题国家”的伊朗、朝鲜等都在卫星发射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足以使美国忧心忡忡。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之外,自2001年美国富商蒂托搭乘俄罗斯“联合号”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以来,外空商业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企业甚至个人成为外空活动主体的时代正日益临近。[19] 今天的外空早已不再如60年前美苏两家独占时那般冷清,美国作为人类社会在外空中的最早进驻者之一,面对越来越多的“邻居”,很自然地会认为活动空间变小,甚至对后来者心存愤懑。
网络空间方面,情况更加复杂。首先,尽管美国在网络技术上仍具有优势,但并不像在海洋和外空方面领先其他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互联网技术问世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不过短短50年,因此美国权力基础并不那么牢固,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也并不悬殊。其次,互联网本身具有开放、自由、流动的特征,行为体接入互联网的成本较低,与海洋、空中和外空相比,更多行为体具有进入网络空间的资源和能力。第三,互联网操作具有不可见、隐蔽的特点,这使得美国难以把握危险来源。考虑到互联网应用早已深入美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安全,如此不可测的安全状态加上控制其他力量主体的难度,足以令美国寝食难安。
海洋方面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新行为体,但对美国来说,诸多新近对海洋投入重大战略精力的国家中,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动向颇值得关注。就其现有实力而言,这些国家或许不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但其在发展海洋力量方面具有更加深刻的经济和全球动机。这些国家使用海上通道、提升海上力量的意愿将随其海外利益的扩展而不断上升。假以时日,美国也许将真正面对一个或几个全面运用海上资源的国家。届时,美国长期以来在海上保有的活动空间和特权将受到冲击,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
二、美国的应对举措与中美战略信任
基于上述主观战略焦虑,美国试图以现有体制和行为规范来束缚全球战略公域的“新到者”,以制度力量来延续美国的特权地位。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规则意识的战略意图所在。但这一举措本身存在重大的合法性问题,因此退回到冷战思维以对抗和争斗的方式打压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便成为美国首选的战略举措,这极大地加剧了中美战略互不信任。
美国试图以软权力扭转其在全球战略公域权力分配中日渐不利的局势面临巨大困难。一方面,无论在海洋、外空还是网络空间,现有规则都存在重大缺陷,尚未形成权威性的全球法治体系。海洋相对而言是比较具有国际规范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被视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该公约基本上反映的是“当时国际社会在海洋问题上所能达成的共识”,仍有“不少条款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有严重缺陷的”,[20] 以致其在处理海洋纠纷时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21] 而且,对于美国来说,它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法通过这一公约来约束竞争对手的行为。在外空方面,当前的国际法律体系主要基于五大条约[22] 和一些宣言,[23] 形成了空间物体登记、损害赔偿、空间营救以及国际合作等四项制度。同样,这些法律文本大多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益难以满足当前需要。[24] 此外,美国在推动国际外空法治建设方面也并不积极,因为对美国来说保持行动自由在多数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美国不愿有强有力的国际法来约束自己的行动和未来的发展。与海洋和外空相比,网络领域的国际法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美国难以依靠全球战略公域中的现有国际规范来约束“新到者”。
另一方面,从美国本身的软实力来看,其道义感召力和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也在不断下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世界各国看到美国为本国利益不惜滥用国际道义、穷兵黩武、不负责任的面目。随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又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否真正值得效仿和照搬。2013年发生的震惊全球的“斯诺登事件”,使美国道义上伪善的一面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样,在一次又一次亲身演绎了道德“失范”之后,美国怎能说服全球战略公域的其他使用者相信其制定的规则是公平、合理、正义的呢?
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的焦躁情绪日益上升。一方面,全球战略公域被认为是美国必须维护之利益,因为这些“通道”是支撑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支柱;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战略公域的法治体系缺失,美国垄断地位的合法性不足日益明显。因此,美国要实施其“控制”全球战略公域的霸权战略,就只能退回到冷战思维,通过重新集结军事同盟的力量,利用对抗和斗争的方式打压新兴国家,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当前的中美博弈中。
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在海洋、外空以及网络等全球战略公域中发展很快,因此成为美国重点防范和打压的对象。首先,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不断收紧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制度,尤其是1998年的《考克斯报告》和1999年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莱迪修正案》,前者恶意诋毁中国,指责中国利用技术交流“偷窃”美国的高科技和军事技术,后者则限制美国在12个领域与中国开展军事交流,至今严重影响着中美军事关系。2006年7月,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发表政策文件,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的范围。2011年6月,美国商务部公布《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再次将中国排除在44个可享受贸易便利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之外。可见,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进步高度戒备。尽管美国曾多次承诺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但始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是其限制中国战略崛起的一部分。
其次,美国在政治上不断抹黑和攻击中国。比如,在海洋问题上,制造“中国海洋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散布中国黑客攻击论,歪曲中国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正常管理;[25] 在外空项目上,制造中国外空力量发展会破坏外空环境的谬论。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绵长海岸线和大规模海外商业往来的国家,中国发展海上力量、走向蓝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网络方面,大量使用美国设备和软件的中国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斯诺登事件”表明,美国对于网络的监控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外空项目上,中国相当谨慎与克制,其对外空环境的影响与美苏外空军备竞赛所造成的危害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显然,美国长期在有关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攻击中国,具有更深刻的政治和战略动机。
第三,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围堵政策。美国通过调整同盟和伙伴关系,通过所谓的“空海一体战”,在中国周边部署和强化导弹防御系统,试图将中国压制在美国编织的网络系统中。因此,美国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的焦虑情绪已经实质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战略互疑的一部分。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如果不能处理好在全球战略公域中的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世界造成破坏性影响。
三、中国应对:恢复全球战略公域的公共性
当然,鉴于全球战略公域的重要性以及中美两国的敏感性,中美在海洋、外空、网络安全等方面事实上已开始接触甚至合作。比如,在海洋问题上,中美除了在反恐、人道主义援助、海上救援等方面继续合作之外,2014年海军高级官员的互动十分频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海军上将不仅在4月份出席了中国主办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而且在7月份再次访华。2014年9月,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赴美参加第21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就中美构建新型海上安全观发表演讲。此外,中国海军还首次参加了美国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6月8日,航行在宫古海峡东南、西太平洋海域的中国北海舰队战备巡逻远海训练舰艇编队还首次运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与美国海军“平克尼”号驱逐舰进行了及时对话。
在网络安全方面,中美也进行了一系列接触。早在2007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就与美国微软公司合作共同举办“中美互联网论坛”。2010年起,中国互联网协会又与美国东西方研究所联合开展有关“中美网络安全对话”课题,并于2013年11月发表了题为《真诚沟通务实合作,共同防范黑客攻击活动》的研究报告。在政府层面,2011年,网络安全就被列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26] 2013年在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博格庄园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同意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平台上建立中美网络安全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的工作在2014年5月后由于美方原因陷入停顿,但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接触与互动并未完全停止。在外空领域,由于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的阻挠,中美合作性的交流和互动推进得十分艰难,但双方政府部门仍在维护外空安全、推进航天合作以及加强战略稳定等方面保持着对话和沟通。
由此可见,海洋、外空和网络等全球战略公域的安全已经成为中美战略沟通的重要内容。但到目前为止的沟通和交往,尚未改变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度。比如,美国仍在强化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布局,试图卡住中国海军走向蓝海的通道;美国有意将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扩大到韩国甚至印度,继续增强对中国的战略核威慑;美国司法部于2014年5月宣布起诉五名中国军人,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在网络领域的关系。如此种种,都说明美国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关心的不是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是要迫使中国服从美国的利益和战略。这样,中美显然难以在全球战略公域中建立起健康、积极、良性互动的关系。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必须改变美国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的错误认知,促使全球战略公域的合作回到正义的轨道上。
首先,中国应该让美国认识到,它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受到历史经验的严重误导,对公域的理解是扭曲的。“全球公域”就其本意而言是指公共领地,指“所有国家都有权使用的资源”[27],具有两大特征:第一,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管辖;第二,具有非排他性,即任何国家都有进入全球公域(包括全球战略公域)的权利。当然,全球公域(如国际水域、外空和网络[28])虽然广阔,但资源仍是有限的。各行为体可能因资源有限而形成竞争关系,但全球公域从法理上对所有国家开放,美国并不具有特殊的权利和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美国由于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先发优势,得以在较长时期内“垄断性”地使用全球战略公域,以至在实践中产生了错觉,似乎美国理所当然应该“主导”全球战略公域,其他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美国的规则和指令。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其他国家相继进入全球战略公域并要求拥有与美国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时,美国就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
从本质上说,美国当前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表现出的战略焦虑是由于其对公域和历史的误读造成的,最终需要美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摆脱和克服。当然,考虑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国际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帮助美国早日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为此,中国应该加强在全球公域尤其是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的理论研究和国际实践,在国际活动中正本清源,还原全球战略公域的公共性质和公益性质。就此而言,中国在外空领域积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的活动,在网络安全领域主张发挥联合国以及其他具有公信力的国际机构的作用,都是正确而具有远见的行动。
其次,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战略公域的制度建设,为全球战略公域实现法治作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是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但是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猜疑的上升,美国不断试图给中国戴上“挑战国际体系”和“改变现状”的帽子。[29] 在政治上试图削弱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道义感召力,在战略上则有可能起到孤立中国的作用。面对美国歪曲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现实,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法治建设。第一,中国应继续就全球战略公域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法律方案和行为准则。如前所述,当今全球战略公域的客观事实是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应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这一体系的更新和完善,而不能置身事外。中国与俄罗斯2008年共同向裁军与谈判会议提出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的草案,[30] 就是对维护和平利用外空、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作出的重要贡献。2013年,面对美国“棱镜”项目对国际信息安全的破坏,中国与俄罗斯又向联合国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也是对全球战略公域秩序的有力维护。中国要持续地用行动维护全球战略公域的公共性。第二,中国应就全球战略公域议题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战略公域的法制建设,不是取代美国或损害美国的利益,而是要保障自己应有的权益。为此,中国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应寻求更大的全球共识和共同愿景,在加强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就维护全球战略公域的和谐与稳定作出协调和安排。第三,维护全球战略公域的和谐与稳定也离不开各国国内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的衔接。因此,中国在参与全球战略公域的法制建设中还应十分注意参与国家间的法律合作与政策协调,进一步拓宽合作面,保障各国在全球战略公域问题上向合作的方向发展,而非走向竞争甚至对抗。
再次,在努力塑造合作性全球战略公域环境的同时,中国要保持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投入与建设,降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中国领导人在深刻判断时代特征、大国关系特点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和政策概念,应该成为引领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31] 目前,美国受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对掌控国际事务和国家间关系的信心有所下降,在处理大国关系中采取“防范对抗”思维方式。对此中国需要使其看清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特征;向其指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相处方式;使其看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并非只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针对美国的心态和顾虑提出的对症之药。中国要在全球战略公域的互动中坚决贯彻超越冷战、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推动中美在全球战略公域形成新型互动关系。
最后,中国要继续加强在全球战略公域的能力建设和战略规划,这是能否引领全球战略公域关系走向正义、合理的力量基础。近年来,得益于正确的发展道路和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运用海洋、大气空间、外空和网络空间的能力大幅提升。在海洋方面,“辽宁号”航母正式交付使用凸显了中国海军走向远洋的能力;在大气空间,2013年中国自主发展的大型运输机运—20试飞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能力;在外空领域,中国不仅发展了载人空间站项目,而且成功研制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打破了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在卫星导航和定位方面的垄断;在网络方面,中国不仅有联想这样的硬件制造商,而且有能够替代微软办公系统的WPS office以及百度、淘宝等网络运营和电商平台。这些力量的发展为中国在全球战略公域中不受制于人或少受制于人作出了贡献。但在欢呼中国在全球战略公域领域进展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当前的力量对于引领全球战略公域走上正义的发展道路尚远远不够。第一,中国为所在地区和世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足。作为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经济能力有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中国为本地区和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正在上升,但却严重缺乏相应的实际能力。一方面,中国的硬件规模仍然比较有限,无论是远洋能力、空中运输能力,还是外空开发或互联网应用,中国现有的设备和设施尚不足以满足地区和世界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硬件条件中还隐藏着很多风险。缺乏自主开发的核心技术,即使在规模上大幅度提高,在运用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存在隐忧。第二,从全球战略公域秩序建设看,中国需要在能力建设的同时关注能力转化。物质条件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基础,但强大的物质条件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道义上的感召力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中国在增加公共物品供应的同时,还要注重与之相关的标准建设、配套建设、网络建设和规范建设。第三,要实现前述两个目标,中国需要尽早出台全球战略公域的“顶层设计”。缺少一套战略规划来指导和管理各种能力建设和部门间协调,中国在全球战略公域竞争中可能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及四处救火的被动局面,难以成为全球战略公域正义秩序的引领者。
结 束 语
总之,全球战略公域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阵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已经由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转向防止新兴大国挑战其全球领导地位。全球战略公域在美国总体实力下降、战略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成为其关注的焦点,被视为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柱。在此背景下,美国在海洋、大气空间、外空以及网络等全球战略公域加大了对中国的制约,它认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全面兴起有可能动摇其垄断和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应在深刻认识美国的战略矛盾和焦虑心态的基础上,积极寻找塑造中美新型全球战略公域关系、引导全球战略公域秩序走向正义与合理的路径。一方面要纠正美国在全球战略公域上对历史的误读;另一方面要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恢复全球战略公域的公共性质。中国引导全球战略公域回到正义、合理的秩序,不是要与美国搞对抗,也不是要争夺“世界霸权”,而是要在国际事务中真正体现新的、符合时代需求的治理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
注释: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2010.
[2]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 Summer 2003, pp. 5-46.
[3] 关于公域问题是如何成为美国军方最高层的关注点的论述,可参见Mark E. Redden and Michael P. Hughes, “Defense Planning Paradigms and the Global Commons,” Joint Force Quarterly, Vol. 60, January 2011, p. 61。
[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2006.
[5] 关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情况可参见 [美]艾伦·H.梅尔泽:《美元为何连年赤字严重》,赵纪萍编译,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19日。
[6]《美国新国防预算拟5年削减10万兵力 增强亚太地区军事存在》,中国日报网,2012年1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01/28/content_14496732.htm。
[7] 关于“优势”战略及美国可以采取的其他战略选项的讨论,可参见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97, pp. 5-53。
[8] 关于全球公域所包含的内容,可参见Susan J. Buck, The Global Commons: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8。
[9] Mark E. Redden and Michael P. Hughes, “Global Commons and Domain Interrelationships: Time for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Strategic Forum, October 2010.
[10] Abraham M. Denmark, “Forg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Comm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5, Iss. 3, May/Jun 2013, p. 132.
[11] 曹升生、夏玉清:《“全球公域”成为新式的美国霸权主义理论——评新美国安全中心及其东北亚战略设计》,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9期,第24-32页。
[12] Gregory F. Treverton, Erik Nemeth and Sinduja Srinivasan, Threats Without Threteners? Exploring Intersections of Threats to the Global Comm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rlington, VA: RAND Corporation, 2012.
[13] “公域”可以是一个国家之内的公共区域,也可以是国家主权管辖之外的人类共有资源、区域或领域,后者被称为“全球公域”。例如,可参见唐双娥:《“全球公域”的法律保护》,载《世界环境》2002年第3期,第21页;韩学晴:《全球公域战略与北约安全新理念》,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4期,第54页。因此,笔者认为,“全球战略公域”概念不仅强调公域的公共性质,还强调其超越国家主权管辖的性质;国家主权管辖之内的公域问题应另行讨论。
[14] 1922年的《五国海军协议》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打破了英国海军长期奉行的“两强战略”,标志着英国的海上霸权走向终结。
[15] 关于美苏早期外空竞争以及美国追赶苏联的经验教训,可参见Wu Chunsi, “Early US Military Space Program: How to Move to the Fast Traffic Lane,” Fud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3, 2006。
[16] John Pike, “The Military Use of Outer Space,” i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2: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13.
[17] Michael E. O’Hanlon, Neither Star War Nor Sanctuary: Constraining the Military Uses of Spa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 42-59.
[18] 《以网络自由名义 美国巩固网络霸权》,新华网,2010年1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31/content_12905664.htm。
[19] 关于外空商业化趋势的发展,可参见李寿平:《外层空间的商业化利用及中国的对策》,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99-104页。
[20] 杨泽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要缺陷及其完善》,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第57页。
[21] 刘中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负面效应分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6期,第82-89页。
[22] 五大条约是指:1967年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循原则的条约》(简称《外空条约》);1968年的《营救宇航员、送回宇航员和归还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简称《营救协定》);1972年的《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简称《责任公约》);1976年的《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简称《登记公约》);1979年的《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简称《月球协定》)。
[23] 这些宣言包括:《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外空宣言》)(1963年)、《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1982)、《关于从外层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1986)、《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1992);《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 并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1996)以及《空间千年:关于空间和人的发展的维也纳宣言》(1999)等。
[24] 关于外空法治体系的缺陷,可参见吴莼思:《外空军控问题》,载杨洁勉主编:《国际体系转型和多边组织发展:中国的应对和抉择》,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25]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绿坝事件”。“绿坝—花季护航”原本是中国工信部推出的一项公益计划,旨在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不良网络信息的危害,这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但在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一些人将项目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引向所谓的中国政府网络审查制度,其别有用心的意图可见一斑。关于绿坝事件的分析,可参见:杜骏飞等:《绿坝事件:信息如何成为权力政治》,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第37-40页。美国对绿坝事件的报道详见:Loretta Chao, “China Squeezes PC Maker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8,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4440211524192081.html。
[26] 晓岸:《网络安全:中美竞合新领域》,载《北京周报》2013年第15期。
[27] Buck, The Global Commons, p. 6.
[28] 关于网络是否是“全球公域”存在争议,参见杨剑:《美国“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的语境矛盾及其本质》,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46-52页。笔者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类似于陆地、海洋或大气空间的维度。与陆地、海洋、大气空间中既有国家主权管辖的部分,也有主权管辖之外的“公域”相类似,网络空间也可能同时存在主权管辖的部分和公域部分。问题是,网络空间的管辖权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全球性的共识。本文将网络列入全球公域问题,讨论的是它可能存在的超出主权管辖的部分。
[29] 有关美国对中国改变现状的指责,可参见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pp. 69-90。
[30] 在2014年6月的裁谈会上,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对该草案提出了更新文件。
[31]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提出的过程,可参见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构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9-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