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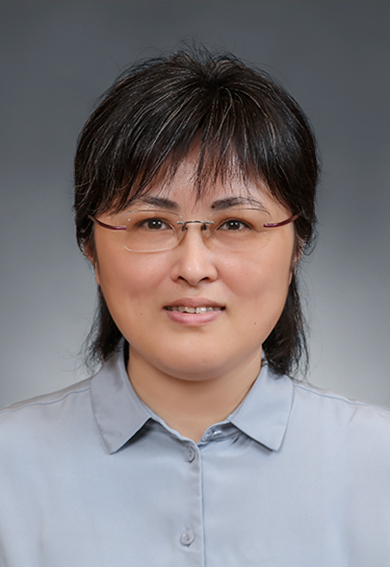
- 吴莼思
- 副研究员
- 美洲研究中心
- 国际战略研究所 所长
- 打造绿色军队:美国军事能源战略调整评析
- 海洋安全视域下的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海军建设
- 试析美国撤军后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空问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台湾学者的观点与角度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及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影响
- 美国“重返亚太”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秩序观”是亚洲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
- “奥巴马主义”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动因和前景
- 民进党南海政策是向美国交心
- 谈菲律宾总统访华
- 从三个方面看美国大选
- 东盟为何未理会南海仲裁案
- 香格里拉对话会防务外交的实质是什么?
- 香格里拉对话会防务外交的实质是什么?
- 菲律宾仲裁案判决与中国之应对
- 谋划南海问题需要战略高度
- 中美需要保持高级别、全方位的战略对话
- 特朗普上台 蔡英文台独梦灭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对亚太安全局势的解读存在重大错误。南中国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以及中美竞争固然影响重大,但亚太地区的重大安全问题远不止于此。首先,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亚太地区饱受民生类安全问题困扰。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包括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4年的印度尼西亚大海啸、2011年的日本核泄漏事故以及2014年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联事件等。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普通公众的经济安全、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而且具有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影响,其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军事安全问题。其次,东亚地区面临巨大的恐怖主义风险,在与东亚紧密相邻的阿富汗地区以及阿拉伯世界正经历着原有秩序解构、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动荡阶段,这些地区中蕴藏的恐怖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因素有可能通过人员流动和教义传播向东亚地区溢出。因此,阿富汗和西亚阿拉伯国家虽然在地理上不属于亚太地区,但其安全形势与东亚国家休戚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国家普遍缺乏油气资源,必须关注西亚阿拉伯世界以及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因此,东亚国家的安全关注不可能局限于亚太区域,东亚国家需要更宽广的安全观。第三,东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不断进步,与此相伴随的是,东亚国家面临许多新课题,如金融创新、技术革命、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运用与保护等。这些新领域普遍存在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而东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又处在社会发展或转型中,尚未做好应对这些新课题的准备,其安全风险可想而知。
可以认为,东亚地区存在诸多安全挑战和风险,将其简化为南中国海问题、钓鱼岛争端和中美竞争等具体问题不仅有失偏颇,更易犯“一叶障目”的战略敌视与战略褊狭错误,其结果是不仅误读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及其性质,更可能导致应对失当,甚至进一步恶化亚太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和地区安全形势。因此,必须从更为全面和战略性的视角考察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及其未来发展。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并不是“中国问题”,相反是亚太安全架构重大转型的体现,其核心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即:随权势转移而来的战略敏感与安全竞争、亚太地区各国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性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导致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下的新型安全挑战特别是规则缺失。尽管这一转型的未来方向尚不明确,但其中后冷战秩序的浮现以及亚洲国家对安全构架的主导权的发展,仍然预示了这一转型的重大意义。唯有准确把握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及其当前趋势,才可能看清亚太安全架构的发展方向,为亚太地区走出目前的安全乱局提出建设性的、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路径选择。
一、亚太安全架构转型的内涵
冷战结束以来,有关亚太地区安全风险的描述主要有两类:一是亚太地区存在两大热点问题,即台海问题和朝核问题;二是亚太地区在冷战结束以后受到更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如金融风险、环境污染、传染病流行、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跨国犯罪等。就特定时段、特定领域而言,这两类描述都较好地反映了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但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以上两种描述已无法概括亚太地区当前的安全状态。首先,台海和朝鲜半岛虽然仍高度敏感,但由于大陆在对台政策上坚持和平发展的方针,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又实行“战略忍耐”[③],台海和朝核问题的“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亚太地区的安全关注正向其他领域发散。其次,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困扰亚太地区,但其热点散乱、暴力冲突的烈度相对不如国家间角力,因此,一旦领土争端和大国竞争重新在亚太地区兴起,地区安全关注便很快由非传统安全问题向传统安全问题转移。第三,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更趋多元化、复杂化。亚太地区不仅有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的地缘政治摩擦、大国竞争相互纠缠,难以通过单维度的手段解决,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于削减传统安全领域的猜疑与竞争功效有限。由此,迫切需要重新思考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本性质与特征。
笔者认为,上述演变事实上暗示着亚太安全架构的某种转型。尽管全球层次上的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便已终结,但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仍在延续。然而,随着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不断上升,各类新兴议题不断涌现,地区安全机制不断发展,亚太地区的冷战架构也在不断受到冲击,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进程已经启动。从当前状态来看,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或者说它正转向应对四方面的安全挑战,其战略后果极可能塑造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
(一)由权势转移引发的战略敏感与安全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普遍受到冲击,迫切需要借助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走出危机。因此,2008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呼吁,在华盛顿举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商讨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这一会议的召开极具象征意义,它表明以往控制世界经济议程的八国集团(G8)正丧失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影响全球议程的能力上升。
与全球层面权力关系调整方向一致,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在亚太地区也呈现上升趋势。除中国之外,印度、越南等国也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影响国家间关系及地区局势的能力有所上升。当然,新兴经济体实力地位的上升势必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其中又以中美关系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全球体系中拥有超强地位。然而,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无所作为,其在东亚的“信用”备受质疑。东南亚国家通过“东盟+1”、“东盟+3”进程加快了与中、日、韩合作的步伐。2001年以后,受打击恐怖主义战略的影响,美国的战略关注长期停留在中东地区,再次错过了与东亚区域合作交汇的时机。然而,与美国对亚太多边合作的冷淡态度不同,中国在1997年之后越来越积极地参与亚太多边合作。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宣布将用10年时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7年11月,中国又与日本、韩国在“东盟+3”平台之外构建了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中国已经成为众多东亚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④] 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网络的中心力量。
这样,当奥巴马政府上台时,美国在东亚地区感受到了来自快速崛起的中国的巨大压力。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快速缩小;[⑤]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迅速发展的区域合作使美国感到其在亚太的经济地位有可能被边缘化,甚至具有被“赶出”亚洲的危险。于是,奥巴马政府祭出了“重返亚洲”的大旗:[⑥] 在经济上,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以抵消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安全上,不断挑动、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竭力破坏东亚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正是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戒备日益上升,导致中美战略互疑居高不下,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中美之间的权力变化成为当前亚太地区众多安全问题的背后因素之一。
考虑到权势转移的当前态势,需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方面,并非只有美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实力地位上升保持敏感,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也同样敏感。长期以来,日本始终是东亚地区的“领头雁”。目前,中国在综合实力、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上均超过日本,日本当权者自然受到巨大冲击,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之间的互动关系。[⑦]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权势转移并非只是朝向中国,地区实力地位上升的国家还包括印度、越南等。印度、越南均在其次区域跃跃欲试,也引发了相关国家的不安,如巴基斯坦相当担忧自身与印度实力差距的拉大,又如东盟国家对越南可能染指东盟领导权颇为担心。可以认为,权势转移对亚太安全架构的挑战或其转型的塑造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二)亚太地区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
在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变化加剧的背景下,2009年5月,亚太地区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成员国递交外大陆架划界案或相关声明的截止日期。围绕这个时间节点,东亚国家纷纷提出其在相关海域的利益诉求,并由此引发了亚太地区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⑧]
2008年11月12日,日本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以“冲之鸟礁”作为基点划出200海里大陆架并以此作为基点延伸出“四国海盆地”、“南硫磺岛地区”以及“九州南部-帕劳海脊地区”等三处外大陆架。2009年2月6日和2月27日,中国和韩国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交声明,明确表达反对意见。
2009年2月17日,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单方面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中业岛等部分岛礁划入菲律宾领土,试图以国内法加强其对南海争议岛礁的主权声索。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历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其他国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领土主权要求,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2009年5月6日,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大片海域作为两国共同的外大陆架。对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严正申明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联合划界案不予审理。
2009年5月7日,越南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当天,中国就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照会,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要求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不审议越南提交的“外大陆架划界案”。
2009年5月11日,我国政府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确定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这份文件确认中国存在外大陆架,但此次提交的信息仅涉及东海大陆架。2009年7月23日,日本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照会表示反对中国提交的文件。
这样,到2009年5月13日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规定的截止日期,东亚国家关于海上领土、海域划界、资源分配的新一轮摩擦已经展开。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亚太国家在海洋权益等问题上确实存在利益冲突,但当前这一轮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并非是由中国挑起的。而这一集中爆发的争端自2009年以来持续处于僵持和紧张状态,表明亚太国家在海洋权益问题上并不愿意妥协。这一态势对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管理这一争端本身及其外部环境,可能极大地推动亚太安全构架的未来转型。
(三)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安全挑战
除了国家间权力变化、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安全问题,东亚国家在过去十多年间还经常受到政局动荡、社会不稳等因素的影响。[⑨] 比如,1999—2001年间,印度尼西亚政局动荡,持续发生种族和宗教冲突,导致数百人死亡。2005年,菲律宾爆发所谓的“第四次人民力量革命”,并在此后几年内持续发生大规模反政府运动,要求时任总统阿罗约下台。自2006年起,泰国政局也陷入持续动荡。所谓的“黄衫军”、“红衫军”争斗不休,以至于时至今日,泰国尚未走出政局动荡的阴霾,不仅旅游业和国际形象大受损伤,而且其在东盟体系以及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被严重削弱。当然,亚太地区受到国内局势困扰的远不止上述国家。越南、缅甸等国的局势近期也颇受关注。这些国家的国内因素与亚太地区的国家间矛盾、利益冲突纠缠在一起,使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棘手。国家转型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安全架构转型的又一个重要因素。[⑩]
然而,国家转型对地区安全架构影响最大的还是自2010年底以来的西亚、北非政治转型。尽管并不属于亚太区域,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转型仍对亚太安全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东亚不乏能源短缺的国家,西亚、北非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如果威胁能源供应,将严重影响东亚国家的安全。第二,东亚国家紧邻阿富汗,西亚、北非政治转型的溢出效应特别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可能通过人员往来、宗教传播等渠道向东亚地区扩散。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从其安全利益出发来界定亚太安全,而不是将其安全利益限定在亚太区域内,由亚太地区来界定东亚国家的安全利益。从这一意义上说,亚太地区的安全也可以是“亚洲的”安全,用亚洲的利益加以界定,用亚洲的方式加以处理。
(四)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挑战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地区安全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以网络安全为例,互联网在当今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互联网应用中也隐藏着巨大风险,对于亚太地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首先,互联网开启了新的领域,但对软硬件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些经济能力比较有限的东亚国家能否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是亚太国家需要面对的第一层考验。其次,互联网的运作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线下运作模式,东亚国家在互联网管理中是否存在风险和漏洞也值得探究。第三,互联网运行的背后承载的是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亚太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多元的价值取向。如何与其他文化和观念交汇共存是东亚国家在互联网应用中面临的新问题。最后,在互联网运用中,违法和犯罪行为可能变得隐秘,东亚国家是否做好准备以应对这一挑战也是一项重要的安全内容。因此,对于亚太国家来说,与若干年前聚焦于台海或朝核问题不同,近些年来互联网、信息等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命题。在这些新的领域中,法制可能尚不完善,技术可能仍在发展,因此更需要亚太国家以前瞻性的措施加以防范与应对。
令人担忧的是,亚太地区在过去的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缺乏风险预防和处置能力。从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核泄漏事件到2014年的马来西亚航空370航班失联事件,东亚国家一再在突发事件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往往需要依赖域外国家的救援。此外,日本核泄漏以及马航航班失联等事件也提示亚太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所谓的安全问题已不仅仅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问题,甚至不仅仅是经济安全问题,而是越来越贴近民生的安全问题,比如粮食安全、生命安全等。亚太地区需要为应对新生的、新型的安全问题做好准备。
总之,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活跃着许多新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以台海或朝核问题为焦点的安全范畴,甚至模糊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分野,突破了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界限。所有这些问题都正挑战着既有的亚太安全架构,同时也正在塑造新的亚太安全架构。
二、亚太安全架构转型的趋势
基于上述对亚太安全架构转型的内涵或挑战的分析,可以认为,当前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崛起”,那样可能导致丧失对亚太安全架构转型的全局性和战略性视野,甚至可能使整个亚太安全架构转型被别有用心者用于“管理”中国崛起,成为针对中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工具。亚太地区当前出现的安全问题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间关系的演化而逐渐形成的。这些问题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时凸显出来,实际上预示着亚太地区安全架构转型的两大趋势,即:地区安全架构正由冷战秩序向后冷战秩序演变,安全议程设置正由超级大国主导向亚洲国家界定演变。
一方面,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正逐渐从冷战秩序向后冷战秩序演变。
亚太地区的冷战秩序远未紧随全球层次的冷战秩序的终结而瓦解。作为冷战的一部分,亚太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在逐渐走出冷战,其主要表现有:第一,亚太国家间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越南加入东盟具有典型意义。东盟成立于1967年,其成立之初,遏制共产主义和柬埔寨问题是促进东盟团结的两大因素,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越南不仅不可能加入东盟,而且实际上是东盟防范和针对的对象。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越南与东盟的关系最终由对抗走向历史性和解,并于1995年成为东盟第七个成员国。[11] 由此,东盟的主要使命由冷战时期的安全对抗逐渐转向区域合作,生动地反映了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变化。
第二,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得到了长足进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更加自觉地走上了寻求地区合作的道路。在区域层面,“东盟 1”、“东盟 3”以及东亚峰会等机制使亚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功能性问题及次区域合作中,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8年末开始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等也都是非常具有特色并致力于取得实际效果的合作平台。亚太地区在过去20多年间涌现出大量多边合作平台,与这一地区在冷战时期表现出的分裂与对抗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亚太地区的主要议题由安全对抗向发展合作方向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亚太国家的注意力纷纷转向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1990—1997年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21%。[12]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亚太地区也面临着众多全球性问题和跨国问题的挑战,如金融危机、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2011年的日本核泄漏事故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合作、民生问题取代军事对抗和地缘政治,成为东亚国家的主要关注。
与亚太地区逐渐走出冷战对抗的步伐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结构向网络化、扁平化的方向发展,这与冷战时期由两大超级大国主导的垂直型国家间关系显然有很大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一些所谓“领导”国家产生失落和焦虑情绪。作为深受冷战格局影响的一个区域,亚太地区要彻底摆脱这种影响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当前,美国在冷战时期在亚太地区编织的军事同盟体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结构。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虽然与其在欧洲的北约体系有所不同,但同样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排他性和意识形态因素。冷战结束以后,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东扩等措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通过参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重新找到了存在的价值。与其相似,美国在亚太地区也不断制造各种威胁论,从“朝鲜核问题”、“中国威胁论”到“南中国海不安全论”等不一而足,为维系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巩固亚太军事同盟提供理由。鉴于军事同盟体系具有内在的排他性和对抗性,这一机制的存在给亚太地区进一步走出冷战结构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亚太地区将最终迎来后冷战时代还是退回冷战的分裂对抗状态,能否处理好军事同盟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指标。
另一方面,亚太安全架构中的东亚国家自主意识正快速增强。
长期以来,亚太安全议程设定受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所控制。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处于两极格局控制下,亚太地区也不得不服从于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失去了自主决定其安全议题的空间。其二,东亚国家对由西方国家设定的议事日程存在某种“路径依赖”。亚洲虽然拥有古老文明,但其进入现代化的时间要比西方国家晚得多。作为现代化过程中起步较晚的群体,东亚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就遇到了已经存在的规则体系,以至于不得不随着外部世界的规则运转,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主导话语权和议事日程的自觉性。
实际上,由于在地理位置、权力地位、经济水平、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很多方面存在差异,西方国家设定的安全议程常常不符合东亚国家的利益和实际,并非东亚国家的核心关切。例如,处于全球权力顶端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其“领导地位”,防止出现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地区力量。因此,亚太国家尤其是东亚主要力量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矛盾对立的状态对其最为有利,这颇类似于历史上霸权国家经常采用的所谓“分而治之”战略。然而,对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其所面临的主要使命是如何保障正在进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规制化得以顺利完成。这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发展问题,可以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大收益。由此可见,美国维护亚太地区“领导权”的利益与东亚国家的发展利益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东亚国家如果一味追随美国的亚太战略,难免在发展利益上受到损失。又如,西方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近些年中将气候变化、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置于议事日程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对于众多东亚国家来说,一方面尚未完成工业化任务,在经济发展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存在较大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均面临诸多比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更加急迫和棘手的安全问题。因此,让东亚国家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优先事项显然并不明智。由此可见,东亚国家应该从其发展阶段、地理位置、文化特点等角度出发,更加自觉地界定安全利益,使亚太地区的安全议程设定更多地体现亚洲国家的需求及特点。
当然,东亚国家控制安全议程的自主性上升,在当前阶段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区域紧张局势,正如亚太地区当前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频发所显示的那样。这是因为东亚国家之间确实存在诸多历史积怨,这些问题在亚太地区安全议程不为自身主导时被长期拖延、压抑下来,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导致了今天更加困难和复杂的局面。东亚国家需要面对这些问题,需要面对当前复杂的局势,在正确界定其安全利益的背景下,寻找更加妥善的方式,处理好相互之间的矛盾,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区域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筑牢基础。
总之,亚太地区当前呈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实质上是这一地区在走出冷战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处理这些矛盾显然不能退回冷战模式,而是要进一步走出冷战格局,完成亚太地区由冷战秩序向后冷战秩序的华丽转身。由此可以看到,维护21世纪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实际上需要更加符合后冷战时代的合作路径,而不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以排他和对抗为特征的同盟关系。
三、亚太安全架构转型的应对战略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些新的安全矛盾,但其根源绝不可能归结于“中国崛起”;恰好相反,这根本上源于本应于冷战结束便启动的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亚太地区要走出冷战阴影,建立更为合理、自主的安全框架,需要更加彻底地消除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阴霾,以21世纪和平发展的方式将亚太地区真正引上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道路。笔者认为,亚太国家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认真打造亚太地区的新型安全秩序。
首先,亚太国家应进一步凝聚共识,认清当前亚太安全问题的基本性质,从亚洲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符合亚太安全发展方向的议事日程。基于亚太安全架构转型本身所具有的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移的特质,亚太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时,必须首先凝聚共识,为地区共同应对安全困局奠定理念基础。为此,中国应该鼓励亚洲国家突破长期以来垄断这一地区的“欧美话语体系”,从亚洲国家的发展利益出发,正确界定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和安全使命,为亚太地区调整国家间关系设立正确方向。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就亚洲安全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新概念。[13] 这些新概念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亚洲事务要以亚洲国家的利益和行为方式作为出发点。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些主张与东盟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倡导的“亚洲精神”以及“东盟方式”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应该成为指导21世纪亚太安全合作的纲领。亚洲国家应抱有坚定走出冷战格局的决心和信心,在新的安全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合作、共赢、互利、互助的新型伙伴关系,为这一地区真正走出冷战秩序作出贡献。当然,在推进亚洲国家的安全主张时,也应十分注意管理亚洲国家的合理预期,防止有些国家因片面强调自身利益或者对地区秩序转型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采取冒险主义行动,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亚太国家应该致力于塑造新的历史背景下应对安全挑战的规范、规则体系。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由规则缺失造成的。其中,有的是因为旧有规则体系正在解体而不再适用,有的则是因为那些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尚未形成完善的行为规范。因此,亚太地区确实需要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安全问题的原则、规范、程序和方式。一方面,对新规范和规则的讨论不能延续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控制模式,而应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符合21世纪特点的新型秩序。为此,中国应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与协调,积极开展有关规则制定的讨论,逐步将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处理引向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真正实现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考虑到亚太安全当前面临的挑战类型,亚太安全架构未来的规范与规则也应当是多层次的,以更为有效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安全挑战为目标,而非寻找某种“万能药”。
第三,亚太地区需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加强了地区合作、多边机制建设的进程,中国也逐步加大了对这一进程的参与力度。从最初阶段的双边交往到参与“东盟 1”和“东盟 3”进程,从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东道国到主动发起亚洲安全合作新架构建设,中国从排斥多边外交走到了参与多边合作,甚至主动设计地区多边机制的阶段。尽管如此,亚太地区的制度建设仍存在诸多弱点,特别是大量多边合作平台常常流于空泛的政策宣示,没有起到实质性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作用。为此,中国应该与地区国家协商,制定更具功能性的地区安全合作议程。因为即便是非传统安全,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从经济、生态、人文到跨国犯罪、非法捕捞,包罗万象。亚太国家必须进一步明确安全合作的重点,以便集中力量获得切实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循环。就当前亚太国家普遍面临的安全问题来看,亚太安全合作的优先事项至少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与保障经济发展有关的安全合作,如能源供应安全、通道运输安全以及经济金融秩序稳定等。第二,与应对暴力冲突有关的安全合作,如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携手应对跨国犯罪,共同加强危机管理,防止危机升级等。第三,与防灾减灾相关的安全合作,如建立区域性的灾害预警和防范机制,设立防灾与减灾国家间合作机制,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对区域性灾害的反应及救援机制等。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亚太地区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与冷战后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相比,亚太地区能够真正用于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政策工具、能力手段和公共物品仍十分有限。在发生重大灾难时,亚太国家仍不得不依赖外部施援,这显然不利于其更主动地掌握亚太安全议程。亚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应加强维护和平的硬件设施。目前,无论是救援物资储备还是远洋能力和空中运输能力建设,抑或是区域援助网络设计,亚洲国家都未就更好地承担起地区安全责任做好准备。第二,亚洲国家需要加强协同能力,使其维护和平的力量构成一个整体,共同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贡献力量。第三,亚洲国家还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21世纪的国际安全与地区事务,与以往相比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其跨领域的特征更加明显,安全已不再局限于军事、政治领域,还涵盖了经济、科技、环境甚至公共卫生领域,要求未来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更为全面和综合地加以理解和处理。亚洲国家的安全团队建设也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总体来看,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需要进一步摆脱冷战思维,以和平、合作、携手共进为新的内核,构建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帮助亚太国家处理好当前的安全矛盾,为亚太地区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安全秩序。
[责任编辑:张 春]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
注释:
[①] “State of the Union: President Obama’s Speech,” ABC News, January 27, 2010, http://abcnews. go.com/Politics/State_of_the_Union/state-of-the-union-2010-president-obama-speech-transcript/story?id=9678572.
[②] 关于中国“示强外交”的讨论,可参见:Andrew Small, “Dealing with A More Assertive China,” Forbes, February 17, 2010; Joshua Cooper Ramo, “Hu’s Visit: Finding a Way Forward on U.S.-China Relations,” Time, April 8, 2010; Robert J. Samuelson, “China First: The Danger behind the Rising Power’s ‘Me First’ Doctrine,” Newsweek, February 16, 2010;等。
[③] 关于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可参见刘俊波:《从“战略忍耐”看奥巴马的对朝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王俊生:《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战略缺失与敌意螺旋的形成》,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9期;许宁、黄凤志:《“战略忍耐”的困境——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剖析》,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等等。
[④] 《胡祖六:中国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凤凰网,2010年1月18日,http://finance. ifeng.com/hybd/special/2010tianxia/20100118/1722824.shtml。
[⑤]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0年4月的数据,中国2001年的GDP总量为13,248.14亿美元,美国为102,861.75亿美元;中国2009年的GDP总量为49,089.82亿美元,美国为142,562.75亿美元。也就是说,2001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10,而到2009年,这一差距缩小到1/3左右。
[⑥] “美国重返亚太”之说始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7月22日在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时的演说。参见Hillary Rodham Clinton, “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ASEAN Summit,” Laguna Phuket, Thail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2, 2009, http://www.state. 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320.htm。
[⑦] 关于权力转移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可参见吴澄秋:《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巴殿君:《“情感文化因素”下的日本战略调整与中日“邻国困境”》,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6期。
[⑧] 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可参见张洁:《对南海断续线的认知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
[⑨] 关于东亚国家国内政治动荡的分析,可参见李文:《东亚民主转型国家与地区的政治与政局》,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2期;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体制的转型:范式、原因和历史任务》,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⑩] 关于国家转型对亚太安全影响的分析,可参见江凌飞:《警惕转型危机冲击亚太》,载《环球时报》2012年12月6日。
[11] 关于东盟与越南关系的分析,可参见周伟、于臻:《试析入盟以前的越南与东盟关系(1975-1995)》,载《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总第145期),第17-23页。
[12] 转引自胡正豪:《中国与东盟关系:国际贸易的视角》,载《国际观察》2001年第2期,第12页。
[13]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5月2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xhy_667356/ zxxx/t115807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