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其成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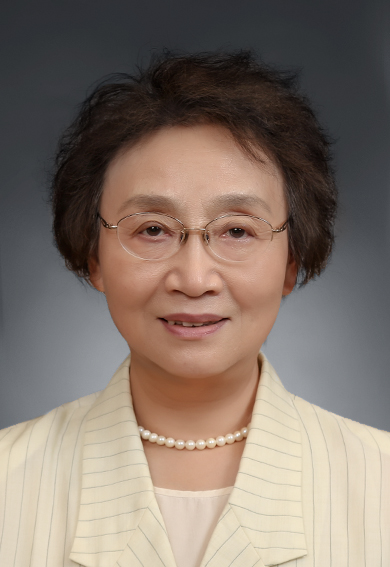
- 李秀石
- 研究员
- 亚太研究中心
- 国际战略研究所
- 新开发银行的发展创新
-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应对与治理
- “中澳对话:G20与地区倡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印度可以为金砖国家合作做出新贡献
-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美国的反恐战略错了
- 中俄关系2015:高调前行、道路曲折
-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深远影响
- 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
- 中国智慧与力量造福世界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
- 金砖国家将建立更密切合作伙伴关系
试析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扩张——从“反海盗”到“保卫”两洋海上通道
李秀石
2014-04-14
日本反海盗
马六甲海峡
索马里亚丁湾
海上通道安全
简介
本文通过研究日本相关法律、政策文件及其实施状况,论证2001年小泉首相倡议缔结亚洲反海盗协定以来,日本立足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和索马里亚丁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反海盗”为契机,构建海上安全合作框架,逐步扩大军事和准军事存在的战略性举措。深入剖析安倍政府宣示“保卫”海上通道的方针政策,解读安倍首相一年多来极力推进的海上通道战略外交,总结日本加强两洋战略扩张的特点。
正文
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十字路口”马六甲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2005年发生102次海盗事件,占世界海盗事件总数的37%[①],在每年约9万4000艘各国过往船舶中,日系船舶占1万4000艘[②]。经苏伊士运河连接欧亚的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每年约有1万8000艘船舶经过,日系船舶约占1700艘,2011年发生了237次海盗事件,占世界海盗事件的一半以上,从2007年起共有3艘日系船舶分别受到海盗登船抢劫、劫持船员及机器破坏的损失[③]。2008~2012年联合国安理会先后10次通过有关反海盗的决议,共有30个国家派军舰赴亚丁湾打击武装海盗。2006年亚洲16国在小泉首相的倡议下,签署《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CAAP)》(亚洲反海盗协定)以来[④],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巡逻艇、护卫舰和预警机等,先后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反海盗”已8年有余。日本作为海盗活动的受害国之一参加反海盗(1999年“阿龙德拉”号船员遭海盗劫持事件即代表案例),但却以此为契机实施海洋战略扩张,首先在两洋扩大军事及准军事存在,建立“公海反海盗体制”,进而宣布“保卫”两洋海上通道。
一、从“反海盗”到“保卫”海上通道的政策演变
1999年至2013年间,以马六甲海峡反海盗为出发点,历届日本政府在前任的基础上不断出台名为反海盗实为扩张海洋战略的新政策,直至安倍二次执政后公然宣示“保卫”两洋海上通道。
日本“第二海军”海保厅进入马六甲海峡“反海盗”颇费周折。1999年小渊首相会晤东盟国家领导人时首次提出合作打击海盗活动的建议。2001年小泉首相正式倡议缔结亚洲反海盗协定。然而,马来西亚和印尼拒绝非沿岸国插手海峡安全事务。两国不仅反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法格提出的解决马六甲海盗问题的区域海洋安全设想(RMSI)[⑤],而且拒绝日本在马六甲海域举行打击海盗多边演习的建议。直到2006年11月根据亚洲反海盗协定的规定在新加坡建立亚洲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ISC),两国仍未在协定上正式签字[⑥]。两国不仅坚持主权至上的立场,马来西亚有国际海事局(IMB)和国际海事组织(IMO)分别设立的接收、汇总并向航行中的船舶免费提供海盗活动信息的海盗报告中心及6个船位通报接收站[⑦],因此不希望在新加坡另立一个反海盗信息中心;印尼则因采取有力措施改善了海峡安全环境,沿岸三国的海军进行联合巡逻而态度消极。日本认识到,在涉及沿岸国主权管辖范围内“反海盗”,必须从改善双边关系入手并具备法律依据。
日本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突破反介入防线,向马来西亚海上法令执行厅(MMEA),派遣海保厅人员作为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的专家提供“技术支援”[⑧],并邀请其参加日泰两国打击马六甲海盗的联合演习;与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合作完成马六甲海峡电子海图的制作[⑨];向印尼提供多项经济援助[⑩],2006~2007年日本用ODA日元贷款帮助印尼在海峡沿岸设立了4个具有自动识别船舶功能、33个应对海难事故和海盗的无线电局,无偿援助其建造3艘巡逻船[⑪]、3艘在日本新建的高速巡逻艇[⑫],促使印尼就“沿岸国与日本关于马六甲海峡航行安全与海洋环境进行长期合作”达成共识[⑬]。2006年日本提供的ODA援助全部覆盖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之间的海上通道沿岸国,包括越南和菲律宾。此后,日本向马六甲海峡派出海保厅巡逻艇“监视海盗”[⑭],通过向ISC提供经费,派遣外交官伊藤嘉章担任最高负责人秘书长以及来自海保厅的“职员”,掌握了这一亚洲多边反海盗机制的主导权。
安倍首次执政后,把反海盗纳入日本海洋战略法制建设,2007年4月推动国会通过《海洋基本法》。该法第21条规定:“确保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运输安全与维持海洋秩序”[⑮];据此,2008年3月福田政府发表《海洋基本计划》,针对“从中东经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到我国周边海域的海上运输通道上,海盗行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规定:(1)重点加强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合作框架建设;以ISC为平台,通过培养人才等提高应对能力。(2)把一揽子应对海盗、走私、偷渡,恐怖活动等海上安全问题,统称为“海洋治安对策与确保航行安全”,支援相关国家提高应对海盗等的能力,与亚洲各国海上治安机构等开展取缔走私、偷渡,恐怖对策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3)提出“研究建立在公海抑制和取缔海盗行为的体制”问题[⑯]。上述政策把反海盗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定位为“海洋治安对策与确保航行安全”,以此为转折点,日本把反海盗活动扩大到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反海盗国际合作的性质。麻生政府为完成“建立在公海抑制和取缔海盗行为的体制”的课题,于2009年6月通过《处罚海盗行为及应对海盗法》(应对海盗法),界定了打击海盗活动的范围是“公海(包括与海洋法相关的联合国条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我国的领海或内水”[⑰]。该规定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1条以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海事组织(IMO)关于“公海打击海盗”的规定[⑱],把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划为日本反海盗的行动范围,表明日本将在其他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内“反海盗”。上述法律及政策文件表明,日本“反海盗”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充分利用ISC平台,通过培养人才扩大海保厅对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及东南亚国家海警的影响。第二,全面应对包括海盗在内的各种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为防卫省自卫队参与构建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创造条件。第三,以建立公海反海盗体制为目标,主导海上安全合作。
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建立了一元化的领导及推进体制。负责安全保障与危机管理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主持“应对索马里亚丁湾海盗相关省厅联络会”的工作。联络会成员包括:内阁危机管理审议官,内阁审议官,内阁官房兼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务局、法务省刑事局、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国土交通省海事局,海上保安厅警备救难部、防卫省运用企划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运用部。这些政府部门在内阁官房的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打破外交、防卫、海上治安等各领域间的界限,从不同角度协作推进列入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预算清单的“反海盗”项目。
民主党执政后,菅直人政府在太平洋“反海盗”四年、派自卫队舰机到印度洋索马里亚丁湾海域为商船护航一年零九个月后,在2010年12月发布的《2011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推出自卫队参与反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等新政策:(1)自卫队在亚太地区与韩、澳、东盟、印度等加强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2)“在亚太地区多层次地组合双边和多边安全保障合作框架使之网络化”。(3)“切实保障从非洲、中东到东亚的海上交通安全等共同利益”[⑲]。新政策把双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的联网提上日程,将自卫队推上国际合作的前台,发挥构建“公海反海盗体制”的主要作用,明确规定保卫“从非洲、中东到东亚”的海上通道是自卫队的职能之一。根据这一新政策,日本从迄今分别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反海盗”,转为在防卫省自卫队的直接参与下,在两洋统一推进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为“保卫”两洋海上通道而努力。从2011年度起,外务省和国土交通省海事局、海保厅分别在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推进的“反海盗”项目,合并为“索马里海域及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对策、确保安全的国际合作”项目 [⑳]。上述政策演变过程表明日本内阁(兼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的决策变化——在反海盗的旗号下,通过自卫队参加国际安全合作,促进双边安全合作框架联网,扩大在“索马里海域及马六甲海峡应对海盗、确保安全的国际合作”的覆盖面,把非洲、中东与东亚之间的海上通道作为贯穿两洋政策的中心线,以“线”带“面”,针对海盗及其他危害海上通道安全的威胁深化国际安全合作,扩大日本的军事存在。
安倍二次执政后,“反海盗”更加名实不符,通过“维持海洋秩序”“保卫”海上通道上升为首要目标,不但正式列入国家安全战略,而且落实在防卫政策中。2013年4月发布的《海洋基本计划》,包括“采取促进维持海洋秩序,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的措施”等内容[21]。12月17日安倍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安保战略)、《2014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2014防卫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14~2018年度)》(2014中期防)。国家安保战略是另外二份政策文件的总纲领,首次明确规定了今后5~10年的安全战略及其实施路径,包括海洋、宇宙、网络、政府开发援助、能源等安保相关的各领域。下面分析与本文论述相关的三份文件的部分内容。
国家安保战略记载日本“应该采取的以外交政策和防卫政策为中心的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抓手”,极力渲染“海洋冲突的危险性”,“南海沿岸国与中国发生围绕主权的争议,给海洋法治、航行自由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带来担忧”。关于海洋安全及两洋通道首次明文规定:“我国作为追求‘开放而稳定的海洋’的海洋国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必须做出“超过以往的积极贡献”——在确保海洋安全上“发挥主导作用”。具体内容包括:(1)对海上通道的各种威胁采取应对海盗等必要措施,在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进与各国的海洋安保合作。(2)我国的海洋监视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加强构筑综合性的国际网络。争取进一步增加与海洋安保相关的双边和多边联合训练等合作的机会并提高质量。(3)合作伙伴为美、澳、韩,“占据我国海上通道要冲的传统伙伴东盟各国”,“位于我国海上通道中央等地缘政治上重要的印度”。(4)与上述伙伴国的合作目标是,支援海上通道的沿岸国等提高海上治安能力,同时与我国共有战略利害的伙伴加强关系,深化相互理解提高共同应对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亚太地区双边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多边安全对话框架及多国联合训练,“与印度在以海洋安全保障为首的广泛领域内加强关系。”(5)具体界定海上通道的地理位置——“经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亚丁湾到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到我国近海的海上通道,对于资源和能源大多依靠海上运输的我国特别重要” [22]。上述规定在2014防卫大纲内落实为“积极推进安保合作”,作为“构建综合机动防卫力量”的组成部分之一[23],在2014中期防内进一步具体化:“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与同盟国等紧密合作,除索马里亚丁湾海盗对策外,支援沿岸国自身的能力。另外,在印度洋及南中国海等我国周边以外的海域,也要利用各种机会,与在海洋安全保障上存在共识的各国充实联合训练和演习。”[24]上列方针政策在国家安保战略的总纲领,防卫方针政策及自卫队的具体职能三个层次上,首次对“保卫”海上通道作出前所未有的明确规定,为日本“发挥主导作用”指明了战略方针、合作伙伴及合作方式,毫不掩饰为扩大其两洋军事存在,拉拢利用与日本在“海洋安全”等方面存在“共识”的国家针对中国强化安全合作的目的。
二、立足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扩大军事存在
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日本之间不存在历史问题,地缘政治因素也不如亚太地区复杂,因此,日本在印度洋扩大军事存在不像在太平洋那样小心翼翼。下面论述日本实施前述方针政策的具体活动。
首先,日本立足马六甲海峡在太平洋地区合纵连横,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准同盟合作协定,积极促进韩国签署同类协定。在此基础上,为构建或加强与东南亚国家海上安全合作框架并促进联网,采取了以下具体步骤。
(一)推动海上安全合作框架联网。2011~2012年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安全保障政策科海上安全保障政策室承担了“在东盟地区论坛内推进海上安全合作”的项目[25]。出于“日本、东盟和美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保持步调一致”的考虑[26],2011年11月17日,野田首相在“日本与东盟”峰会上倡议,创建东亚峰会的下级机构“东亚海洋论坛”制定海上航行安全的原则,在东盟没有响应的情况下[27],日本转为主要利用声索国实现目的。(二)安倍政府力促日菲双边合作升级,承诺以ODA方式援助10艘巡逻艇等加强菲方海警能力,2013年2月创立两国外交、海警、海军“3 3”海上安全磋商框架[28]。7月安倍访菲, 双方决定“在两国防卫当局和海上治安机构之间加强联合训练等实践性合作和各种交流”[29]。(三)提升日越海洋安全合作,复制日菲“3 3”框架。2013年1月安倍访越与阮晋勇总理会谈,提供5亿美元贷款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和安全、政治及外交领域的政策协调[30]。12月安倍再次会晤阮晋勇,承诺新增1000亿日元贷款,双方“关于日本向越南海警提供巡逻船等开始具体协商达成共识”[31]。安倍还向印尼许诺提供约620亿日元贷款,印尼同意与日本建立外交与防卫当局的“2 2”磋商框架[32];试图与新加坡建立“3 3”框架[33];敦促马来西亚与日本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34]。
以上事实证明,安倍政府不遗余力推广“2 2”、“3 3”框架,主要目的是使自卫队参与由外务省及海保厅唱主角的合作框架,在扩大准军事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海洋安全磋商、举行联合训练和演习扩大军事存在,主导亚太海上安全事务,通过构筑“中国包围网”牵制中国在东海应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
其次,在印度洋地区,日本立足索马里亚丁湾扩大军事存在。
2009年3月,麻生首相发布“海上警备行动命令”[35],陆海空自卫队组建两支反海盗部队派往印度洋:海上部队由海自的2艘护卫舰及补给舰组成,航空部队是“混合任务部队”,包括P-3C预警机(最多时4架)、以及C130H运输机等运输物资和人员的空自部队和担任警戒的陆自部队[36]。其中,预警机2009年3月~2013年4月底累计飞行约6,300小时,向其他国家的反海盗军舰和过往商船提供信息约7,300次[37],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提供“公共产品”扩大了国际影响,二是提高了实战能力,三是为日本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恰当的理由——预警机需要着陆、补给和维修设施,为实现自卫队不但“派出去”而且“留下来”做出了贡献。2009年3月日本外务省在吉布提设立了联络处,2012年1月升级为大使馆。2011年7月7日,P-3C预警机部队在吉布提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正式挂牌[38]。这不仅是日本二战后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也是有史以来首个设在非洲基地。
为推进“保卫”海上通道的政策,从2013年12月10日起,海自在亚丁湾“反海盗”的护卫舰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护航,另一路加入美英等15个国家的军舰组成的多国部队“第151联合任务部队”(CTF151),分担特定海域的警戒任务[39]。海自正式参加“防护海域自愿者联盟”执行任务,不仅有利于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海军紧密合作,而且能够增加情报来源,可以从位于亚丁湾以外的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各国海军获取情报[40]。对于急欲实现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倍政府而言,还有以外促内的政治意义:在同一海域执行同一任务的其他国家的军舰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海自能否援救是国内争论的焦点之一。安倍设立的咨询机构“重构安全保障法制基础恳谈会”的代理会长北冈伸一透露:“保卫海上通道”作为必须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状况”之一,将写入恳谈会的研究报告[41]。海自加入CTF151已成事实,势必促进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速度。由此可见,陆海空自卫队齐聚亚丁湾“反海盗”,内外兼顾,取得划时代的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印度洋反海盗部队与外务省、海保厅及JICA共同落实“应对索马里亚丁湾海盗相关省厅联络会”决定的“反海盗”措施。日本以吉布提为战略支点,与索马里及其周边的非洲国家构建了名曰“协商反海盗相关方会议”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开展“制定国际规则等环境建设”活动,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海洋秩序”。2012年10月,海保厅邀请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阿曼、也门的海警负责人,在东京举办“中东、东非地区海上治安机构高级工作会议”;10~11月JICA为吉布提等国的海警举办了“海上犯罪研修”[42]。此外,日本在援助索马里的名义下,向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扩大军事存在。日本声称2007年后共向索马里提供2亿9,39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43]。实际上,其中包括援助设在肯尼亚的联合国维和(PKO)中心、回收销毁“非洲之角”小型武器等由自卫队承担的“技术援助”项目,这是为了与受援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打开突破口的惯用做法。
再次,整合两洋海上安全合作。2013年9月24~26日,外务省把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通道的沿岸国,与中国存在岛礁主权争议的声索国等13个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高级将领及海警负责人召集到东京开会。会议以“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政策”为主题,外务政务官城内実在致辞中强调“多边协调对于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号召各国接受日本的积极援助[44]。此次会议名曰“支援新兴海洋国家能力建设讲座”,为各国提供海保厅的技术,提高各国的海上警备能力,“目的则在于协调各国联合行动,其中包括牵制加强海洋进出的中国”[45]。日本已经向埃及和苏丹派遣了自卫队常驻人员,2014年度还将向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和南非派驻,通过各种路径扩大在非洲特别是印度洋沿岸国的军事存在。
总之,日本在过去8年间,从在两洋“反海盗”起步,逐步在军事上扩大存在,在外交上整合两洋海上安全合作框架,不但努力构建“公海反海盗体制”,而且力图规范“海洋秩序”,为实现“保卫”两洋通道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三、安倍首相的海上通道战略外交
访问海上通道沿岸国在安倍“俯瞰地球仪的战略外交”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安倍首相及防卫相等通过多次出访“与日本共有战略利害的伙伴加强关系”,从东南亚10国到中东海合会(GCC)6国,再到非洲的吉布提、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南亚的印度,几乎囊括两洋海上通道的沿岸国。解读若干个案如下。
(一)2013年8月24日,安倍为深化经济与海上安全合作访问巴林,整合现有交流关系建立“2 2”安保协商框架是主要目的之一。安倍与马哈德国王举行会谈并发表《日本与巴林王国加强“面向稳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安倍强调两国在政治和安保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关于包括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及应对海盗在内的海上安全保障,防扩散,反恐对策,人道主义援助及救灾等,在两国外交部及国防部和巴林内务部之间实施安保对话。双方还希望根据2012年4月签订的防务交流备忘录,进一步促进业务交流、部队间交流及包括多边合作在内的防务交流[46]。新设日巴“2 2”框架及时协调政策,对于日本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与海合会密切经济与安全合作,确保能源资源进口和海上通道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2013年8月27日,安倍访问吉布提与盖莱总统会谈:“位于海上通道要冲的吉布提是日本战略上的重要伙伴”,日本要为提高吉布提的海上治安能力做贡献——从9月起关于向吉方海警提供巡逻艇展开调查,并派遣海上执法专家等提高海警的业务能力[47]。另据媒体披露,安倍政府将与吉方协商扩充吉布提基地,建立自卫队的补给和中转基地;对海自在印度洋的“活动据点”吉布提港,投入47亿日元建设停机坪、机库和补给仓库等设施[48]。这才是日本援助吉布提的深层含义。
(三)2014年1月9日,安倍访问凸显“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阿曼,堪称海上通道战略外交之最。从安倍与卡布斯国王发布的《加强日本国与阿曼国“面向稳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来看,除促进阿曼对日出口石油及天然气等合作外,双方强调海上通道的重要性,“一致认为考虑到阿曼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有必要加强包括应对海盗在内的海上安保合作”。卡布斯国王重申,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为确保海湾地区和平稳定的海路继续努力”,“双方重申了面向这一目标承担的义务及准备,表明促进各层次的防卫交流的意愿”[49]。阿曼的塞拉来港位于亚丁湾通道与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战略要冲,能够兼顾两条海上通道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日本已将该港作为海自在印度洋反海盗舰队的“活动据点”之一。不难看出,在双方“承担的义务及准备”的表述背后,还有目前不能公布的秘密。
(四)“与位于海上通道中央的印度”继续加强海洋安保合作。 2014年1月6日,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访印举行防长会谈,决定两国海军开展“反恐等方面的交流”,年内举行第三次海军联合训练,促进陆海空三军的合作交流[50]。25~27日安倍访印,双方发布《加强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安倍感谢印度邀请海自参加下次印美“马拉巴尔”海上联合训练——这是日方一再攻关的结果。双方决定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建立定期协商机制[51],年内举行第4次防卫政策对话等,重申“定期、更加频繁地继续实施两国海上联合训练的决心。双方不仅促进有关海上问题的双边及多边合作,而且决定“日印合作启动有关东盟的协商”[52]。日印海上安全合作已有14年之久。海保厅与印度海警自2000年每年举行联合演练和海警负责人互访[53]。所谓日印海军联合训练是日本构筑“中国包围网”的重要举措之一。在2012年6月的首次演习中,双方“以舰队协作为重点”进行了“基础性训练”,2013年12月即升级为海上射击和反潜作战的实战训练,“帮助印度海军学习海自的反潜搜索等提高保卫海上通道的能力,符合日印两国的利益”[54]。
以上事实证明,“保卫”两洋通道既是日本“反海盗”政策演变的结果,也是安倍政府加强海洋战略扩张并实行“对中遏制”的体现,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日本已在印度洋沿岸战略要地建立了一个空自及陆自部队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吉布提,三个海自部队的“活动据点”——在吉布提港和亚丁港,呈“钳形”扼住连接红海和阿拉伯海的咽喉,控制亚丁湾通道;从塞拉莱港可兼顾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两条通道。上述海上通道战略外交的轨迹显示,日本在两洋的军事存在不断膨胀。而日本媒体却在“贼喊捉贼”:安倍访非包括牵制中国的意图,因为“中国正在非洲东岸的印度洋谋求确保霸权”[55],“日印防务全面合作——中国企图向印度洋发展”[56]。
包括印度在内,日本利用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声索国“制衡中国”有多重目的:其一,鼓励支持声索国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挑事,分散中国应对日本“购岛”的精力,减轻日本的压力。其二,发动舆论战,释放中国“海洋活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烟雾,掩盖日本实施海洋扩张的事实。其三,促使美国更加担心“中国威胁”,离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到为日本改变战后秩序建设“能战国家”进一步“松绑”的目的。
四、日本推行两洋战略扩张的实质及其特点
日本抓住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机遇,全力推进海洋战略扩张,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战略东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日美同盟的“相互运用性”。另一方面,日本激化日韩之间的岛争及历史矛盾,干扰、迟滞了美国推进美日韩军事合作的进程。尤其是暴露出欲将美国拖入中日钓鱼岛武力冲突,企图主导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意图,以及为将来取代美国做准备的长远打算。所以,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是利用加防范,目前以利用为主。
对中国而言,安倍政府推行的有关海上通道的政策,具有企图用控制海上交通咽喉的“质”,弥补日本与中国抗衡的“量”的不足的战略意图——不仅在东海与中国全面对抗,而且在连接两洋的海上通道上构筑“防线”,在更大范围内形成遏制中国的战略优势。平时对中国构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威慑,战时对中国的能源资源等进出口贸易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不能忽视或低估日本的深谋远虑。
日本从“反海盗”到控制两洋海上通道的战略扩张具有以下特点。
(一)参加反海盗“相关省厅联络会”的政府各部门横向紧密协作。(1)外务省“从战略高度运用ODA”,重点援助两洋通道的沿岸国加强海警能力建设,鼓励支持声索国对中国挑衅。(2)国土交通省海事局和海保厅从扩大非传统安全合作打开突破口,通过援助对象国的海警,在扩大准军事力量存在的同时,为自卫队加入双边海上安全合作、特别是为海自军舰建立“活动据点”创造条件。(3)法务省刑事局参与“反海盗”,使日本具备对海盗进行“法庭审判”的条件,同时拓展了支援两洋通道沿岸国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的合作空间。(4)海保厅、防卫省、外务省等“3 3”海上安全磋商框架,打破了准军事与军事合作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双边协调政策。在内阁官房(兼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务局)的一元化统辖下,上列部门不受行政机构间“条块分割”的限制,是日本实施海洋战略扩张的根本保障。
(二)政府各部之间的协作具有“非同步配合”和“同步配合”的特点。在日本曾经侵略邻国、中日政治博弈敏感度高等地缘政治因素复杂的太平洋地区,外务省与海保厅先行打开局面、防卫省随后加入合作框架的协作方式,集中体现了非同步配合的特点。相反,在地缘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印度洋地区,海上保安官搭乘海自护卫舰“反海盗”、护卫舰与预警机搭配、空自与陆自部队混编进驻基地的派遣方式,集中体现了同步配合的特点。其结果是,同步实现陆海空自卫队及海保厅的海外派遣,有利于促进综合安全合作。日本在吉布提从开设联络处、设立大使馆,到建立军事基地并在吉布提港立足,再到援助海警并扩建基地和港口的一系列举措,即外务省、防卫省、海保厅及JICA等同步配合的典型。
(三)安倍政府的海洋战略扩张,具有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相契合的一面。安倍在国家安保战略中界定海上通道之前,在巴林会见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米勒,强调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后日本将切实负起稳定这一地区的责任”,“表明了加强干预中东地区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的意向”[57]。安倍声称将援助非洲3﹒2亿美元,其中包括向美国主导的“中非国际援助使命”项目提供300万美元[58]。安倍是自民党屈指可数的亲美派,深知美国军方的影响力,以军促政,在对美外交上走捷径;以外压内,在国内政治上减少阻力。
(四)日本善于向国际组织“借壳”推进两洋政策。日本向国际海事组织(IMO)醵资1,460万美元创设信托基金,支援也门、肯尼亚、坦桑尼亚建立并运营海盗信息中心(ISC),并且将训练基地设在吉布提,为日本在印度洋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此外,日本还向提高反海盗能力的国际信托基金醵资350万美元,用于联合国组织实施的取缔索马里亚丁湾海盗、帮助索马里周边国家建立补充起诉海盗的制度[59]。通过“借壳”国际组织提供援助,有利于降低受援国对日本介入内政的警惕。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日本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2010年4月日本向IMO下属的应对索马里海盗小组派驻了海保厅人员,安倍政府已决定今后继续为此而努力。
(五)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观察,日本的海洋战略扩张活动呈现以行动倒逼立法和修改法律的特点。麻生政府在国会立法三个月之前向印度洋派出反海盗部队,以既成事实促进立法;安倍政府则命令在印度洋护航的海自护卫舰,加入CTF151多国部队分担特定海域警戒任务,倒逼行使集体自卫权解禁。这既是日本的“议会政治”蜕变为“自民党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社会政治生态整体右倾化的必然反映。
最后,日本推行两洋战略扩张,既有国家安保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有具体政策法规,辅以经济合作尤其是ODA援助,大力促进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效果。对中国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影响形成新挑战,或将形成中国以经济合作为主,日本经济安全并举,在“海上通道安全”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日本在修订2011防卫大纲时已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安倍二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偏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轨道,对此,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充分重视,拓宽视野,妥善应对。
一、从“反海盗”到“保卫”海上通道的政策演变
1999年至2013年间,以马六甲海峡反海盗为出发点,历届日本政府在前任的基础上不断出台名为反海盗实为扩张海洋战略的新政策,直至安倍二次执政后公然宣示“保卫”两洋海上通道。
日本“第二海军”海保厅进入马六甲海峡“反海盗”颇费周折。1999年小渊首相会晤东盟国家领导人时首次提出合作打击海盗活动的建议。2001年小泉首相正式倡议缔结亚洲反海盗协定。然而,马来西亚和印尼拒绝非沿岸国插手海峡安全事务。两国不仅反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法格提出的解决马六甲海盗问题的区域海洋安全设想(RMSI)[⑤],而且拒绝日本在马六甲海域举行打击海盗多边演习的建议。直到2006年11月根据亚洲反海盗协定的规定在新加坡建立亚洲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ISC),两国仍未在协定上正式签字[⑥]。两国不仅坚持主权至上的立场,马来西亚有国际海事局(IMB)和国际海事组织(IMO)分别设立的接收、汇总并向航行中的船舶免费提供海盗活动信息的海盗报告中心及6个船位通报接收站[⑦],因此不希望在新加坡另立一个反海盗信息中心;印尼则因采取有力措施改善了海峡安全环境,沿岸三国的海军进行联合巡逻而态度消极。日本认识到,在涉及沿岸国主权管辖范围内“反海盗”,必须从改善双边关系入手并具备法律依据。
日本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突破反介入防线,向马来西亚海上法令执行厅(MMEA),派遣海保厅人员作为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的专家提供“技术支援”[⑧],并邀请其参加日泰两国打击马六甲海盗的联合演习;与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合作完成马六甲海峡电子海图的制作[⑨];向印尼提供多项经济援助[⑩],2006~2007年日本用ODA日元贷款帮助印尼在海峡沿岸设立了4个具有自动识别船舶功能、33个应对海难事故和海盗的无线电局,无偿援助其建造3艘巡逻船[⑪]、3艘在日本新建的高速巡逻艇[⑫],促使印尼就“沿岸国与日本关于马六甲海峡航行安全与海洋环境进行长期合作”达成共识[⑬]。2006年日本提供的ODA援助全部覆盖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之间的海上通道沿岸国,包括越南和菲律宾。此后,日本向马六甲海峡派出海保厅巡逻艇“监视海盗”[⑭],通过向ISC提供经费,派遣外交官伊藤嘉章担任最高负责人秘书长以及来自海保厅的“职员”,掌握了这一亚洲多边反海盗机制的主导权。
安倍首次执政后,把反海盗纳入日本海洋战略法制建设,2007年4月推动国会通过《海洋基本法》。该法第21条规定:“确保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运输安全与维持海洋秩序”[⑮];据此,2008年3月福田政府发表《海洋基本计划》,针对“从中东经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到我国周边海域的海上运输通道上,海盗行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规定:(1)重点加强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合作框架建设;以ISC为平台,通过培养人才等提高应对能力。(2)把一揽子应对海盗、走私、偷渡,恐怖活动等海上安全问题,统称为“海洋治安对策与确保航行安全”,支援相关国家提高应对海盗等的能力,与亚洲各国海上治安机构等开展取缔走私、偷渡,恐怖对策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3)提出“研究建立在公海抑制和取缔海盗行为的体制”问题[⑯]。上述政策把反海盗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定位为“海洋治安对策与确保航行安全”,以此为转折点,日本把反海盗活动扩大到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反海盗国际合作的性质。麻生政府为完成“建立在公海抑制和取缔海盗行为的体制”的课题,于2009年6月通过《处罚海盗行为及应对海盗法》(应对海盗法),界定了打击海盗活动的范围是“公海(包括与海洋法相关的联合国条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我国的领海或内水”[⑰]。该规定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1条以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海事组织(IMO)关于“公海打击海盗”的规定[⑱],把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划为日本反海盗的行动范围,表明日本将在其他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内“反海盗”。上述法律及政策文件表明,日本“反海盗”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充分利用ISC平台,通过培养人才扩大海保厅对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及东南亚国家海警的影响。第二,全面应对包括海盗在内的各种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为防卫省自卫队参与构建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创造条件。第三,以建立公海反海盗体制为目标,主导海上安全合作。
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建立了一元化的领导及推进体制。负责安全保障与危机管理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主持“应对索马里亚丁湾海盗相关省厅联络会”的工作。联络会成员包括:内阁危机管理审议官,内阁审议官,内阁官房兼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务局、法务省刑事局、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国土交通省海事局,海上保安厅警备救难部、防卫省运用企划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运用部。这些政府部门在内阁官房的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打破外交、防卫、海上治安等各领域间的界限,从不同角度协作推进列入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预算清单的“反海盗”项目。
民主党执政后,菅直人政府在太平洋“反海盗”四年、派自卫队舰机到印度洋索马里亚丁湾海域为商船护航一年零九个月后,在2010年12月发布的《2011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推出自卫队参与反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等新政策:(1)自卫队在亚太地区与韩、澳、东盟、印度等加强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2)“在亚太地区多层次地组合双边和多边安全保障合作框架使之网络化”。(3)“切实保障从非洲、中东到东亚的海上交通安全等共同利益”[⑲]。新政策把双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的联网提上日程,将自卫队推上国际合作的前台,发挥构建“公海反海盗体制”的主要作用,明确规定保卫“从非洲、中东到东亚”的海上通道是自卫队的职能之一。根据这一新政策,日本从迄今分别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反海盗”,转为在防卫省自卫队的直接参与下,在两洋统一推进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为“保卫”两洋海上通道而努力。从2011年度起,外务省和国土交通省海事局、海保厅分别在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推进的“反海盗”项目,合并为“索马里海域及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对策、确保安全的国际合作”项目 [⑳]。上述政策演变过程表明日本内阁(兼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的决策变化——在反海盗的旗号下,通过自卫队参加国际安全合作,促进双边安全合作框架联网,扩大在“索马里海域及马六甲海峡应对海盗、确保安全的国际合作”的覆盖面,把非洲、中东与东亚之间的海上通道作为贯穿两洋政策的中心线,以“线”带“面”,针对海盗及其他危害海上通道安全的威胁深化国际安全合作,扩大日本的军事存在。
安倍二次执政后,“反海盗”更加名实不符,通过“维持海洋秩序”“保卫”海上通道上升为首要目标,不但正式列入国家安全战略,而且落实在防卫政策中。2013年4月发布的《海洋基本计划》,包括“采取促进维持海洋秩序,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的措施”等内容[21]。12月17日安倍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安保战略)、《2014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2014防卫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14~2018年度)》(2014中期防)。国家安保战略是另外二份政策文件的总纲领,首次明确规定了今后5~10年的安全战略及其实施路径,包括海洋、宇宙、网络、政府开发援助、能源等安保相关的各领域。下面分析与本文论述相关的三份文件的部分内容。
国家安保战略记载日本“应该采取的以外交政策和防卫政策为中心的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抓手”,极力渲染“海洋冲突的危险性”,“南海沿岸国与中国发生围绕主权的争议,给海洋法治、航行自由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带来担忧”。关于海洋安全及两洋通道首次明文规定:“我国作为追求‘开放而稳定的海洋’的海洋国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必须做出“超过以往的积极贡献”——在确保海洋安全上“发挥主导作用”。具体内容包括:(1)对海上通道的各种威胁采取应对海盗等必要措施,在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进与各国的海洋安保合作。(2)我国的海洋监视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加强构筑综合性的国际网络。争取进一步增加与海洋安保相关的双边和多边联合训练等合作的机会并提高质量。(3)合作伙伴为美、澳、韩,“占据我国海上通道要冲的传统伙伴东盟各国”,“位于我国海上通道中央等地缘政治上重要的印度”。(4)与上述伙伴国的合作目标是,支援海上通道的沿岸国等提高海上治安能力,同时与我国共有战略利害的伙伴加强关系,深化相互理解提高共同应对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亚太地区双边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多边安全对话框架及多国联合训练,“与印度在以海洋安全保障为首的广泛领域内加强关系。”(5)具体界定海上通道的地理位置——“经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亚丁湾到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到我国近海的海上通道,对于资源和能源大多依靠海上运输的我国特别重要” [22]。上述规定在2014防卫大纲内落实为“积极推进安保合作”,作为“构建综合机动防卫力量”的组成部分之一[23],在2014中期防内进一步具体化:“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与同盟国等紧密合作,除索马里亚丁湾海盗对策外,支援沿岸国自身的能力。另外,在印度洋及南中国海等我国周边以外的海域,也要利用各种机会,与在海洋安全保障上存在共识的各国充实联合训练和演习。”[24]上列方针政策在国家安保战略的总纲领,防卫方针政策及自卫队的具体职能三个层次上,首次对“保卫”海上通道作出前所未有的明确规定,为日本“发挥主导作用”指明了战略方针、合作伙伴及合作方式,毫不掩饰为扩大其两洋军事存在,拉拢利用与日本在“海洋安全”等方面存在“共识”的国家针对中国强化安全合作的目的。
二、立足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扩大军事存在
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日本之间不存在历史问题,地缘政治因素也不如亚太地区复杂,因此,日本在印度洋扩大军事存在不像在太平洋那样小心翼翼。下面论述日本实施前述方针政策的具体活动。
首先,日本立足马六甲海峡在太平洋地区合纵连横,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准同盟合作协定,积极促进韩国签署同类协定。在此基础上,为构建或加强与东南亚国家海上安全合作框架并促进联网,采取了以下具体步骤。
(一)推动海上安全合作框架联网。2011~2012年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安全保障政策科海上安全保障政策室承担了“在东盟地区论坛内推进海上安全合作”的项目[25]。出于“日本、东盟和美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保持步调一致”的考虑[26],2011年11月17日,野田首相在“日本与东盟”峰会上倡议,创建东亚峰会的下级机构“东亚海洋论坛”制定海上航行安全的原则,在东盟没有响应的情况下[27],日本转为主要利用声索国实现目的。(二)安倍政府力促日菲双边合作升级,承诺以ODA方式援助10艘巡逻艇等加强菲方海警能力,2013年2月创立两国外交、海警、海军“3 3”海上安全磋商框架[28]。7月安倍访菲, 双方决定“在两国防卫当局和海上治安机构之间加强联合训练等实践性合作和各种交流”[29]。(三)提升日越海洋安全合作,复制日菲“3 3”框架。2013年1月安倍访越与阮晋勇总理会谈,提供5亿美元贷款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和安全、政治及外交领域的政策协调[30]。12月安倍再次会晤阮晋勇,承诺新增1000亿日元贷款,双方“关于日本向越南海警提供巡逻船等开始具体协商达成共识”[31]。安倍还向印尼许诺提供约620亿日元贷款,印尼同意与日本建立外交与防卫当局的“2 2”磋商框架[32];试图与新加坡建立“3 3”框架[33];敦促马来西亚与日本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34]。
以上事实证明,安倍政府不遗余力推广“2 2”、“3 3”框架,主要目的是使自卫队参与由外务省及海保厅唱主角的合作框架,在扩大准军事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海洋安全磋商、举行联合训练和演习扩大军事存在,主导亚太海上安全事务,通过构筑“中国包围网”牵制中国在东海应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
其次,在印度洋地区,日本立足索马里亚丁湾扩大军事存在。
2009年3月,麻生首相发布“海上警备行动命令”[35],陆海空自卫队组建两支反海盗部队派往印度洋:海上部队由海自的2艘护卫舰及补给舰组成,航空部队是“混合任务部队”,包括P-3C预警机(最多时4架)、以及C130H运输机等运输物资和人员的空自部队和担任警戒的陆自部队[36]。其中,预警机2009年3月~2013年4月底累计飞行约6,300小时,向其他国家的反海盗军舰和过往商船提供信息约7,300次[37],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提供“公共产品”扩大了国际影响,二是提高了实战能力,三是为日本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恰当的理由——预警机需要着陆、补给和维修设施,为实现自卫队不但“派出去”而且“留下来”做出了贡献。2009年3月日本外务省在吉布提设立了联络处,2012年1月升级为大使馆。2011年7月7日,P-3C预警机部队在吉布提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正式挂牌[38]。这不仅是日本二战后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也是有史以来首个设在非洲基地。
为推进“保卫”海上通道的政策,从2013年12月10日起,海自在亚丁湾“反海盗”的护卫舰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护航,另一路加入美英等15个国家的军舰组成的多国部队“第151联合任务部队”(CTF151),分担特定海域的警戒任务[39]。海自正式参加“防护海域自愿者联盟”执行任务,不仅有利于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海军紧密合作,而且能够增加情报来源,可以从位于亚丁湾以外的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各国海军获取情报[40]。对于急欲实现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倍政府而言,还有以外促内的政治意义:在同一海域执行同一任务的其他国家的军舰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海自能否援救是国内争论的焦点之一。安倍设立的咨询机构“重构安全保障法制基础恳谈会”的代理会长北冈伸一透露:“保卫海上通道”作为必须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状况”之一,将写入恳谈会的研究报告[41]。海自加入CTF151已成事实,势必促进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速度。由此可见,陆海空自卫队齐聚亚丁湾“反海盗”,内外兼顾,取得划时代的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印度洋反海盗部队与外务省、海保厅及JICA共同落实“应对索马里亚丁湾海盗相关省厅联络会”决定的“反海盗”措施。日本以吉布提为战略支点,与索马里及其周边的非洲国家构建了名曰“协商反海盗相关方会议”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开展“制定国际规则等环境建设”活动,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海洋秩序”。2012年10月,海保厅邀请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阿曼、也门的海警负责人,在东京举办“中东、东非地区海上治安机构高级工作会议”;10~11月JICA为吉布提等国的海警举办了“海上犯罪研修”[42]。此外,日本在援助索马里的名义下,向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扩大军事存在。日本声称2007年后共向索马里提供2亿9,39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43]。实际上,其中包括援助设在肯尼亚的联合国维和(PKO)中心、回收销毁“非洲之角”小型武器等由自卫队承担的“技术援助”项目,这是为了与受援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打开突破口的惯用做法。
再次,整合两洋海上安全合作。2013年9月24~26日,外务省把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通道的沿岸国,与中国存在岛礁主权争议的声索国等13个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高级将领及海警负责人召集到东京开会。会议以“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政策”为主题,外务政务官城内実在致辞中强调“多边协调对于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号召各国接受日本的积极援助[44]。此次会议名曰“支援新兴海洋国家能力建设讲座”,为各国提供海保厅的技术,提高各国的海上警备能力,“目的则在于协调各国联合行动,其中包括牵制加强海洋进出的中国”[45]。日本已经向埃及和苏丹派遣了自卫队常驻人员,2014年度还将向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和南非派驻,通过各种路径扩大在非洲特别是印度洋沿岸国的军事存在。
总之,日本在过去8年间,从在两洋“反海盗”起步,逐步在军事上扩大存在,在外交上整合两洋海上安全合作框架,不但努力构建“公海反海盗体制”,而且力图规范“海洋秩序”,为实现“保卫”两洋通道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三、安倍首相的海上通道战略外交
访问海上通道沿岸国在安倍“俯瞰地球仪的战略外交”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安倍首相及防卫相等通过多次出访“与日本共有战略利害的伙伴加强关系”,从东南亚10国到中东海合会(GCC)6国,再到非洲的吉布提、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南亚的印度,几乎囊括两洋海上通道的沿岸国。解读若干个案如下。
(一)2013年8月24日,安倍为深化经济与海上安全合作访问巴林,整合现有交流关系建立“2 2”安保协商框架是主要目的之一。安倍与马哈德国王举行会谈并发表《日本与巴林王国加强“面向稳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安倍强调两国在政治和安保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关于包括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及应对海盗在内的海上安全保障,防扩散,反恐对策,人道主义援助及救灾等,在两国外交部及国防部和巴林内务部之间实施安保对话。双方还希望根据2012年4月签订的防务交流备忘录,进一步促进业务交流、部队间交流及包括多边合作在内的防务交流[46]。新设日巴“2 2”框架及时协调政策,对于日本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与海合会密切经济与安全合作,确保能源资源进口和海上通道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2013年8月27日,安倍访问吉布提与盖莱总统会谈:“位于海上通道要冲的吉布提是日本战略上的重要伙伴”,日本要为提高吉布提的海上治安能力做贡献——从9月起关于向吉方海警提供巡逻艇展开调查,并派遣海上执法专家等提高海警的业务能力[47]。另据媒体披露,安倍政府将与吉方协商扩充吉布提基地,建立自卫队的补给和中转基地;对海自在印度洋的“活动据点”吉布提港,投入47亿日元建设停机坪、机库和补给仓库等设施[48]。这才是日本援助吉布提的深层含义。
(三)2014年1月9日,安倍访问凸显“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阿曼,堪称海上通道战略外交之最。从安倍与卡布斯国王发布的《加强日本国与阿曼国“面向稳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来看,除促进阿曼对日出口石油及天然气等合作外,双方强调海上通道的重要性,“一致认为考虑到阿曼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有必要加强包括应对海盗在内的海上安保合作”。卡布斯国王重申,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为确保海湾地区和平稳定的海路继续努力”,“双方重申了面向这一目标承担的义务及准备,表明促进各层次的防卫交流的意愿”[49]。阿曼的塞拉来港位于亚丁湾通道与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战略要冲,能够兼顾两条海上通道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日本已将该港作为海自在印度洋反海盗舰队的“活动据点”之一。不难看出,在双方“承担的义务及准备”的表述背后,还有目前不能公布的秘密。
(四)“与位于海上通道中央的印度”继续加强海洋安保合作。 2014年1月6日,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访印举行防长会谈,决定两国海军开展“反恐等方面的交流”,年内举行第三次海军联合训练,促进陆海空三军的合作交流[50]。25~27日安倍访印,双方发布《加强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安倍感谢印度邀请海自参加下次印美“马拉巴尔”海上联合训练——这是日方一再攻关的结果。双方决定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建立定期协商机制[51],年内举行第4次防卫政策对话等,重申“定期、更加频繁地继续实施两国海上联合训练的决心。双方不仅促进有关海上问题的双边及多边合作,而且决定“日印合作启动有关东盟的协商”[52]。日印海上安全合作已有14年之久。海保厅与印度海警自2000年每年举行联合演练和海警负责人互访[53]。所谓日印海军联合训练是日本构筑“中国包围网”的重要举措之一。在2012年6月的首次演习中,双方“以舰队协作为重点”进行了“基础性训练”,2013年12月即升级为海上射击和反潜作战的实战训练,“帮助印度海军学习海自的反潜搜索等提高保卫海上通道的能力,符合日印两国的利益”[54]。
以上事实证明,“保卫”两洋通道既是日本“反海盗”政策演变的结果,也是安倍政府加强海洋战略扩张并实行“对中遏制”的体现,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日本已在印度洋沿岸战略要地建立了一个空自及陆自部队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吉布提,三个海自部队的“活动据点”——在吉布提港和亚丁港,呈“钳形”扼住连接红海和阿拉伯海的咽喉,控制亚丁湾通道;从塞拉莱港可兼顾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两条通道。上述海上通道战略外交的轨迹显示,日本在两洋的军事存在不断膨胀。而日本媒体却在“贼喊捉贼”:安倍访非包括牵制中国的意图,因为“中国正在非洲东岸的印度洋谋求确保霸权”[55],“日印防务全面合作——中国企图向印度洋发展”[56]。
包括印度在内,日本利用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声索国“制衡中国”有多重目的:其一,鼓励支持声索国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挑事,分散中国应对日本“购岛”的精力,减轻日本的压力。其二,发动舆论战,释放中国“海洋活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烟雾,掩盖日本实施海洋扩张的事实。其三,促使美国更加担心“中国威胁”,离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到为日本改变战后秩序建设“能战国家”进一步“松绑”的目的。
四、日本推行两洋战略扩张的实质及其特点
日本抓住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机遇,全力推进海洋战略扩张,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战略东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日美同盟的“相互运用性”。另一方面,日本激化日韩之间的岛争及历史矛盾,干扰、迟滞了美国推进美日韩军事合作的进程。尤其是暴露出欲将美国拖入中日钓鱼岛武力冲突,企图主导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意图,以及为将来取代美国做准备的长远打算。所以,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是利用加防范,目前以利用为主。
对中国而言,安倍政府推行的有关海上通道的政策,具有企图用控制海上交通咽喉的“质”,弥补日本与中国抗衡的“量”的不足的战略意图——不仅在东海与中国全面对抗,而且在连接两洋的海上通道上构筑“防线”,在更大范围内形成遏制中国的战略优势。平时对中国构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威慑,战时对中国的能源资源等进出口贸易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不能忽视或低估日本的深谋远虑。
日本从“反海盗”到控制两洋海上通道的战略扩张具有以下特点。
(一)参加反海盗“相关省厅联络会”的政府各部门横向紧密协作。(1)外务省“从战略高度运用ODA”,重点援助两洋通道的沿岸国加强海警能力建设,鼓励支持声索国对中国挑衅。(2)国土交通省海事局和海保厅从扩大非传统安全合作打开突破口,通过援助对象国的海警,在扩大准军事力量存在的同时,为自卫队加入双边海上安全合作、特别是为海自军舰建立“活动据点”创造条件。(3)法务省刑事局参与“反海盗”,使日本具备对海盗进行“法庭审判”的条件,同时拓展了支援两洋通道沿岸国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的合作空间。(4)海保厅、防卫省、外务省等“3 3”海上安全磋商框架,打破了准军事与军事合作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双边协调政策。在内阁官房(兼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务局)的一元化统辖下,上列部门不受行政机构间“条块分割”的限制,是日本实施海洋战略扩张的根本保障。
(二)政府各部之间的协作具有“非同步配合”和“同步配合”的特点。在日本曾经侵略邻国、中日政治博弈敏感度高等地缘政治因素复杂的太平洋地区,外务省与海保厅先行打开局面、防卫省随后加入合作框架的协作方式,集中体现了非同步配合的特点。相反,在地缘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印度洋地区,海上保安官搭乘海自护卫舰“反海盗”、护卫舰与预警机搭配、空自与陆自部队混编进驻基地的派遣方式,集中体现了同步配合的特点。其结果是,同步实现陆海空自卫队及海保厅的海外派遣,有利于促进综合安全合作。日本在吉布提从开设联络处、设立大使馆,到建立军事基地并在吉布提港立足,再到援助海警并扩建基地和港口的一系列举措,即外务省、防卫省、海保厅及JICA等同步配合的典型。
(三)安倍政府的海洋战略扩张,具有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相契合的一面。安倍在国家安保战略中界定海上通道之前,在巴林会见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米勒,强调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后日本将切实负起稳定这一地区的责任”,“表明了加强干预中东地区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的意向”[57]。安倍声称将援助非洲3﹒2亿美元,其中包括向美国主导的“中非国际援助使命”项目提供300万美元[58]。安倍是自民党屈指可数的亲美派,深知美国军方的影响力,以军促政,在对美外交上走捷径;以外压内,在国内政治上减少阻力。
(四)日本善于向国际组织“借壳”推进两洋政策。日本向国际海事组织(IMO)醵资1,460万美元创设信托基金,支援也门、肯尼亚、坦桑尼亚建立并运营海盗信息中心(ISC),并且将训练基地设在吉布提,为日本在印度洋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此外,日本还向提高反海盗能力的国际信托基金醵资350万美元,用于联合国组织实施的取缔索马里亚丁湾海盗、帮助索马里周边国家建立补充起诉海盗的制度[59]。通过“借壳”国际组织提供援助,有利于降低受援国对日本介入内政的警惕。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日本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2010年4月日本向IMO下属的应对索马里海盗小组派驻了海保厅人员,安倍政府已决定今后继续为此而努力。
(五)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观察,日本的海洋战略扩张活动呈现以行动倒逼立法和修改法律的特点。麻生政府在国会立法三个月之前向印度洋派出反海盗部队,以既成事实促进立法;安倍政府则命令在印度洋护航的海自护卫舰,加入CTF151多国部队分担特定海域警戒任务,倒逼行使集体自卫权解禁。这既是日本的“议会政治”蜕变为“自民党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社会政治生态整体右倾化的必然反映。
最后,日本推行两洋战略扩张,既有国家安保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有具体政策法规,辅以经济合作尤其是ODA援助,大力促进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效果。对中国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影响形成新挑战,或将形成中国以经济合作为主,日本经济安全并举,在“海上通道安全”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日本在修订2011防卫大纲时已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安倍二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偏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轨道,对此,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充分重视,拓宽视野,妥善应对。
文献来源:《国际观察》
注释:
[①]日本外務省:『ODA白書 2006年版』、「第I部第2章第6節 海の安全確保へのアジア沿岸諸国への支援-マラッカ海峡の安全航行への施策-」、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6_hakusho/index.html、下载日期2013年7月20日。[②]日系船舶:船籍为日本或属于日本船舶公司的外籍船舶,雇佣船员中少有日本人。
[③]内閣官房ソマリア沖・アデン湾における海賊対処に関する関係省庁連絡会:「2012年 海賊対処レポート」、『ソマリア海賊による日本関係船舶の海賊被害状況(2007年~2011年)』、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siryou2/report2012.pdf、下载日期2013年8月20日。
[④]亚洲反海盗协定的缔结国是东盟10 国和中、韩、日、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
[⑤] 羽原敬二:「海上保安庁による海事セキュリティの展開と強化」、www.kansai-u.ac.jp/ILS/PDF/nomos22-03.pdf、下载日期2013年8月20日。
[⑥] 蔡鹏鸿:“日本主导东南亚反海盗合作机制对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三期;羽原敬二「海上保安庁による海事セキュリティの展開と強化」。
[⑦]1998年国际海事组织(IMO)在马六甲海峡实行强制性的大型船舶通报船位制度,共设立9个接收站,有6个设在马来西亚。日本参議院:「重要事項調査議員団(第三班)報告書」、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kokusai_kankei/jyuyoujikou/h18/h183houkoku.html、下载日期2013年7月20日。
[⑧]日本参議院:「重要事項調査議員団(第三班)報告書」。
[⑨]日本外務省:『ODA白書 2006年版』、「第I部第2章第6節 海の安全確保へのアジア沿岸諸国への支援-マラッカ海峡の安全航行への施策-」。
[⑩]日本外務省:「日本・インドネシア共同声明『新たな挑戦へのパートナー』」、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onesia/ji_seimei/kh_a.html、下载日期2013年8月20日。
[⑪]日本外務省:『ODA白書 2006年版』、「第I部第2章第6節 海の安全確保へのアジア沿岸諸国への支援-マラッカ海峡の安全航行への施策-」。
[⑫]『世界の艦船』2008年(平成20年)1月号(通巻684号)、海人社发行、第50頁。
[⑬]内閣官邸:「海洋問題に関する日・インドネシア共同発表」(平成17年6月2日)、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5/06/02press4.html、下载日期2013年8月20日。
[⑭]日本外務省:『ODA白書 2006年版』「第I部第2章第6節 海の安全確保へのアジア沿岸諸国への支援-マラッカ海峡の安全航行への施策-」。
[⑮]「海洋基本法」(平成19年4月27日法律第33号)、
http://law.e-gov.go.jp/announce/H19HO033.html、下载日期2007年5月12日。
[⑯]総合海洋政策本部:「海洋基本計画」(平成20年3月18日)、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080318kihonkeikaku、下载日期2007年5月12日。
[⑰]「海賊行為の処罰及び海賊行為への対処に関する法律」(平成21年6月24日法律第55号)最終改正:平成24年9月5日法律第71号、http://www.cas.go.jp/jp/hourei/houritu/kaizoku_houritsu.pdf、下载日期20012年10月1日。
[⑱]国际商会下属的国际海事局(IMB)发布的海盗定义与海洋法公约和IMO不同:没有必要区分海盗行为发生在公海还是发生在领土国家海域内,也不需要发生在两船之间,海盗攻击也可以包括政治目的。陈志瑞等:“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⑲]「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平成22年12月17日)、第8頁、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0/1217boueitaikou.pdf、下载日期2010年12月22日。
[⑳]综合海洋政策本部:「H23年度海洋関連予算一覧表」、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ichiran_h23.pdf、下载日期2011年4月10日。
[21]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海洋基本計画」(平成25年4月)、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下载日期2013年4月20日。
[22]「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第1~3、14、21頁、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下载日期2010年12月22日。
[23]「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第12頁、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下载日期2010年12月22日。
[24]「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26年度~平成30年度)について」、第12頁、1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chuki_seibi26-30.pdf1、下载日期2010年12月22日。
[25]综合海洋政策本部:「H24年度海洋関連予算一覧表」、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sisaku/ichiran_h24.pdf、下载日期2012年4月22日。
[26]日本政府决定倡议新设“东亚海洋论坛”,《读卖新闻》2011年9月28日。
[27]蒋丰:“日本包围网受挫,东盟发展离不开中国”,《日本新华侨报》2011年11月21日,引自中新网2011年11月21日电。
[28]日本外務省:「第2回日・フィリピン海洋協議の開催について(結果概要)」(平成25年2月22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5/2/0222_04.html、下载日期2013年2月30日。
[29]日本外務省:「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概要)」(平成25年7月27日)、http://www.mofa.go.jp/mofaj/shin/shin16_000003.html、下载日期2013年8月1日。
[30]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ベトナム訪問(概要)」(平成25年1月17日)、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vti_1301/vietnam.html、下载日期2013年1月28日。
[31]日本外務省:「日ベトナム首脳会談(概要)」(平成25年12月15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18_000142.html、下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32]日本外務省:「日・インドネシア首脳会談(概要)」(平成25年12月13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22_000793.html、下载日期2013年12月20日。
[33]日本外務省:「第3回日・シンガポール海上安全保障対話の開催(結果概要)」(平成25年7月23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6_000457.html、下载日期2013年7月30日。
[34]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日・マレーシア首脳会談及びナジブ首相主催晩餐会(概要)」(平成25年7月25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4_000130.html、下载日期2013年7月30日。
[35]按照“海上警备行动命令”,反海盗部队最初只能为日系船舶护航,三个月后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海盗法》后,护航对象扩大到所有船舶。
[36] ソマリア沖海賊の対策部隊派遣出典: 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
[37]内閣官房ソマリア沖・アデン湾における海賊対処に関する関係省庁連絡会:「2012年 海賊対処レポート」。
[38]日本外務省:「ソマリア沖・アデン湾の海賊等事案の現状と取り組み」(平成25年5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pirate/africa.html#our-country-effort4、下载日期2013年7月30日。
[39]「ソマリア沖の海自護衛艦、国際艦隊の下で活動開始」、『産経新聞』2013年12月11日。
[40]「『集団的自衛権』想定、海自の海賊対処、新局面も ソマリア沖、各国と初の本格任務」、『産経新聞』2013年11月19日。
[41]「安保法制懇報告書、シーレーンやサイバー、宇宙も、北岡座長代理」、『産経新聞』2013年8月8日。
[42]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务局:「平成25年度海洋関連予算(概算要求)の概要」、第44頁、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sanyo/dai10/siryou2.pdf、下载日期2013年12月11日。
[43]「ソマリア沖・アデン湾の海賊等事案の現状と取り組み」(平成25年5月)。
[44]「外務省、中国をけん制『力による現状変更は認められない』、海上交通路で初セミナー」、『産経新聞』2013年9月25日。
[45]「外務省:新興海洋国に警備セミナー」、『毎日新聞』2013年9月25日、東京朝刊。
[46]日本外務省:「日本とバーレーン王国との間の『安定と繁栄に向けた包括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に関する共同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2181.pdf、下载日期2013年12月1日。
[47]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ジブチ訪問」(平成25年8月27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4_000156.html、下载日期2013年12月1日。
[48] 《产经新闻》2013年11月7日。
[49]日本外務省:「日本国とオマーン国との間の安定と繁栄に向けた包括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に関する共同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3761.pdf、下载日期2013年12月1日。
[50]「自衛隊とインド軍が対テロ交流 日印防衛相会談」、『産経新聞』2014年1月7日。
[51]日本外務省:「共同声明日インド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5063.pdf、下载日期2014年1月30日。
[52]日本外務省:「日・インド首脳会談(概要)」(平成26年1月25日)、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632.html、下载日期2014年1月30日。
[53] 外務省南西アジア課:「最近のインド情勢と日インド関係」(2014年1月)、
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0898.pdf、下载日期2014年1月30日。
[54]「首相、訪印から帰国 対中意識、積極外交でシーレーン安全確保へ着々」、『産経新聞』2014年1月28日。
[55]「安倍首相、アフリカ外交強化、年明け訪問伝達へ、対中国牽制、海上安全・資源で協力」、『産経新聞』2013年9月26日。
[56]「日印防衛相会談、陸・空も交流強化へ…中国視野」、『読売新聞』2014年1月7日。
[57] 「『日本にとって死活的問題』、首相、シーレーン安全確保に意欲、ネックは集団的自衛権、中東歴訪」、『産経新聞』2013年8月26日。
[58]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アフリカ政策スピーチ、『一人、ひとり』を強くする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2014年1月14日於:AU本部・アディスアベバ)、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3954.pdf、下载日期2014年1月30日。
[59]日本外務省:「ソマリア沖・アデン湾の海賊等事案の現状と取り組み」(平成25年5月)。
